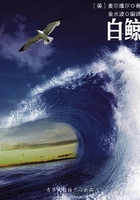
第19章 船(1)
我们躺在床上盘算着明天该怎么安排。但使我吃惊且颇为担心的是:隗魁告诉我,他已经多次和约约——这是那尊小黑神的名字——通灵问话,约约也对他说过两三遍,总之它非常坚决主张,不要两个人一起到停在港口的捕鲸船中间去,不要一起去挑选下海的船只,约约很认真地吩咐说,挑选船只的事应该完全由我一个人去办,因为约约有意要帮助我们,所以约约已经挑好了船只,这船如果让我伊希米尔自己去,也一定会发现的,因为它全像是偶然出现似的;而且我要做的就是马上上船去做水手,暂时不要理会隗魁。
我忘了说,在许多事情上,隗魁对小黑神杰出的判断力和惊人的预见性深信不疑,异常尊敬,认为它是非常灵验的神,总能准确预测但并非所有仁慈的安排都是成功。
我一点也不喜欢。隗魁的这个计划,或者更不如说是约约的计划,即关于挑选船只的事情,我倒是很想凭着隗魁的智慧选出一条最适合我们搭乘、又能稳稳当当搭载我们财物的船只。可我所有的辩解,隗魁都当成了耳边风,我只好答应下来;所以我下了狠心,全力以赴,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得漂漂亮亮。第二天清早,我留下隗魁和约约在我们的小卧房里闭门不出,安享他们禁食、禁欲和祈祷的日子。那些清规戒律,我总也并不明白。随他们去吧,我只管跑了去找船。我转悠了很久,又当成漫无目的地问了许多人,总算打听到了有三条船,它们都是要出航三年才回来的:“魔闸号”、“珍馐号”和“裴廓德号”。“魔闸号”的来历我不清楚,“珍馐号”不用说,至于“裴廓德号”嘛,你肯定还记得,那是马萨诸塞州印第安人中很有名望的一支部落,如今和古代米狄斯人一样都绝了种。我查看了“魔闸号”,又打听了它的情况;接着又跳上“珍馐号”;最后才来到“裴廓德号”,仔仔细细的查看了一遍,然后拿定主意:这就是我们要坐的船。
读此书时,读者或许已经见过许多古老的船只,比如方头的横帆船、形体巨大的日本舢板、黄油箱似的配备了帆和桨的快艇,等等;但请你相信我,像“裴廓德号”这样难得一见的古船,你肯定没看到过。它是一艘风格古朴的船,要说有什么与众不同,就是外形很小,像一只带爪的脚,古色古香的。它长年漂泊于四大洋上,历经岁月沧桑,饱受台风海浪的洗礼,古老的船身黑黝黝的,像一名远征过埃及和西伯利亚的法国投弹士兵。年高德劭的船首像是满脸髭须似的。桅杆像古代科隆三位老王的背脊笔直地立着——这桅杆是在原来的桅杆被风吹坏后,于日本海岸砍来的。古老的甲板已经破旧,起了皱,就像关纪念坎特伯乔教堂培基特大主教,也有一些新奇的玩意儿立起来的供朝圣者顶礼膜拜的大石板一样。但是船上除这些古迹之外,还添加了一些奇特的新东西,让人想起五十多年来它走过的艰难历程。老船长法勒,任船上的大副多手,后来有了自己的船才卸任,这位老法勒,作为“裴廓德号”的主要股东之一,在就任大副期间,在它本就奇特的外表上,把船进行了精心选材,和巧妙设计,到头来只有11世纪的丹麦海盗头子索基尔·赫克雕刻的圆盾和床架才可以与之媲美。它那没有嵌木板的、敞开着的船舷整个儿被装饰得像一只伸长的下巴,上面布满了抹香鲸的牙齿,像栓子一样在它上面系着作为船体肌腱的旧麻绳。这些肌腱缚着的不是陆地林中的劣质木材,而是灵巧地穿过用海象牙齿做成的滑轮。船不屑在最重要的舵上装备旋轮,而是颇具幽默感地装上了舵柄;舵柄是一整块材料,是用它的世代冤仇的狭长的下颚骨精心雕刻出来的。它是一条高贵而忧伤的船。一切高贵的东西都难免让人产生这种感觉。
这时我扫视了一下后甲板,想找一个在船上有权威的人,以便毛遂自荐当水手,可是,一开始一个人也找不到,但在主桅后面,一个样子古怪的帐篷,或者就说是小屋子,引起我的注意。圆锥形,约十英尺高,用露脊鲸颚骨正中和顶部石板似的又大又长的软组织它:大头朝下,一块块地在甲板上铺成环状,然后用绳子捆结实,倾斜着一块搭着一块,在正中形成一个毛丛丛的尖顶,蓬松的须毛忽左忽右地摆动着,像古代波托沃塔米酋长的发髻。三角形的出入口朝船首敞开,所以里面的人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船首的一举一动。
在这个古怪的房子里,我总算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人,看样子还像个管事的。现在正值中午,船上没什么事,他也不必发号施令,所以正休息着。他坐在一张古式的橡木椅子上,椅子上上下下都刻满了稀奇古怪的图案;椅子的底座交错拼着一大堆富有弹性的软骨,和这小屋用料是一样的。
或许,我所看到的这个上了岁数的人,在外表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肤色呈棕褐色,肌肉结实,像许多年迈水手一样,身上厚厚实实地裹着一件教友会信徒款式的蓝色舵工装;只是他的眼眶周围纵横交错着许多极细小的皱纹,不借助显微镜简直还看不见。这是由于经常在大风中顶风观察而造成的肌肉紧缩所留下来的。这样的眼纹在生气时是很有威慑力的。
“您就是‘裴廓德号’的船长吗?”我走到帐篷门口问了一声。
“就算我是,你找船长干什么?”他咄咄逼人。“我想当水手。”
“你想当,是吗?我看你不像南塔基人——你在漏水的船上干过水手?”
“没有,先生,从没干过。”“对捕鲸这行当一窍不通,我敢肯定——呃?”“是的,先生。但我保证,我很快就可以学会。我在商船上当过几回水手,我想——”“该死的商船水手。别跟我说那些鬼话。你看那条腿?你再敢跟我胡扯商船水手的事,我就叫你的腿和屁股分家啰。商船水手,算什么!我看你现在对干过商船水手很自豪吧。不过算你走运,伙计!你是为什么想要去捕鲸的呢,呃?这很可疑,不是吗?你说。——你干过海盗,是吗?——你抢劫过那商船的船长,有这事吗?——你出海的时候,会对船上的头头们起歹念吗?”
我表情坚定地声明,我从未干过这类事情。我看得出,在这半是幽默半是挖苦的话语后面,这个老水手,这个与世隔绝的教友会信徒式的南塔基人,脑子里装满了岛民的偏见。除了科德角人和维因耶德人,他们不相信任何外地人。
“说说,你想要去捕鲸和原因是什么呢?我弄清了这个,才考虑雇你当水手。”
“好的,先生,我想看看捕鲸是怎么回事?我想去见识见识。”
“想看看捕鲸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知道亚哈船长吗?”
“亚哈船长是谁,先生?”“哦,哦,我就知道你不知道。亚哈船长是这船的船长。”
“这么说,是我弄错了。我还以为我是在和船长本人说话呢。”
“你是在和法勒船长说话——法勒船长在听你说话,小伙子。‘裴廓德号’这次出海,是由我和比勒达船长负责准备,备齐船上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水手。我们两个都是股东和代理人。不过,我要告诉你,假如你真想知道捕鲸是怎么回事,我倒是在你签字画押绝不反悔之前,有一个法子让你了解一下。小伙子,去看看亚哈船长吧,你会发现他只有一条腿。”
“你的意思是……被大鲸给弄去了一条?”“是大鲸弄去的!小伙子,我跟你说:是一条曾经把一只小艇打得粉碎的无比凶恶的抹香鲸把腿咬断,嚼碎,嚼得咯吱咯吱响!——唉!唉!”
他憋足了劲的神态着实把我镇住了,最后两声发自内心的痛苦呻吟,也很让我为之震撼,但我尽量保持神态自然,说:“你说的肯定错不了,先生,可是我怎么知道那条鲸竟会如此十恶不赦呢,说实在的,我可以从这简单的事故中推知许多情形。”
“你看你,小伙子,你还嫩了点,明白吗;不过还数你不好吹嘘。当然啰,你是出过海的,可这算得了什么?”
“先生,”我说,“我记得我跟你说出过四次海,是在商——”
“你别再说了!记得对商船水手有何感想吗——别惹我烦——我不想听。不过,话总得说明白。我已经给你挑明了捕鲸是怎么回事?你还想去捕鲸吗?”
“没错,先生。”
“很好,那么,你敢把鱼叉刺进一条活鲸的喉咙,再穷追不舍吗?你说,快告诉我!”
“我敢,先生。如果非这么干不可的话,或者说不这样就会被鲸干掉的话,我会敢的。可我认为不会有这种情况。”
“太好了。你不仅想去亲身体验一下捕鲸是怎么回事?还想开开眼界?你是这样说的吗?我记得。那么,往前走,走到那个风口子上去瞧瞧,然后回来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一时间里,我被这荒唐的要求弄呆了,我该怎么办,是一笑置之还是果真照办。直到法勒船长怒目圆睁瞪着我,才赶紧去看。
我走到前边,在风口处看了一会儿,我看到船在翻滚的潮水中落了锚但仍在剧烈摇摆,现在正侧着船舷面临辽阔的洋面。洋面无边无际,但非常单调而又冷峻,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好吧,说来听听,”我一回来,法勒就说,“你看到了什么?”
“没大收获,”我回答说,“到处是水,不过视野倒很宽广。另外,我想风暴快来了。”
“那么,你想要怎么去见世面呢?你是想绕行合恩角,再多开开眼界,呃?在你站着的地方就不能见世面吗?”
我有点哽住了,但捕鲸是一定要去的,我也会去的;而“裴廓德号”是一艘很不错的船——我想是再好不过了——我于是把上述想法又对法勒说了一遍。他看我决心这么坚决,就表示愿意雇我当水手。
“你可以马上就签约,”他补充了一句,“你跟我来。”说完,他领我走下甲板,进了船舱。
坐在船尾横木上的人在我看来是一个气势特殊、惊世骇俗的人物。原来他就是比勒达船长,和法勒船长一样,他也是这艘船最大的股东之一;其他股份,在这些港口可能是由领年金的老人持有,还有那些寡妇、孤儿以及受监护的未成年人。
比勒达和法勒一样,是教友会信徒,事实上许多南塔基人都是教友会信徒,这个岛本来就是这个教派的人定居的地方;如今,岛上居民大部分保持着浓厚的教友会特征,只是受到异域情调的影响程度有所减轻罢了。
在这些教友会信徒中,有些是穷凶极恶的水手和捕鲸人。他们凶狠好斗,他们有仇必报。
所以在男性当中,许多人是以《圣经》中的名字来命名的——这在岛上已是司空见惯的时尚——他们很小就学会了使用教友会习语中那种高雅且极其吸引人的称谓词汇;后来,他们那种敢作敢为、英勇无畏、充满无限冒险的生活,奇妙地与那种固有的不变的特点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勇往直前、浑身是胆的性格,这种性格简直称得上是斯堪的纳维亚的海中之王,或者是具有诗人气质的罗马异教徒。当这些品质和一个力大无穷、具有高超的智慧和丰富情感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又在极遥远的北方水域、在此处目力不及的天空星座下忍受寂寥和孤苦度过了无数个漫长的值班之夜的时候,就会突破传统的束缚,特立独行;再加上在大自然宽容大度的襟怀中,吸取了各种柔美的、粗犷的气质,同样也得益于偶然的机缘,使他学会了豪放、简洁和高雅的语言——这样的人在全国上下也是万里挑一的,他可是为上演崇高的悲剧而造就的完美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