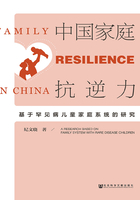
第二节 罕见病儿童家庭压力和影响因素研究回顾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家庭在其发展历程中都有可能面临来自预期或不期而至的压力。Holmes和Minoru据此制定了一个经过调整的家庭压力事件排序表,在43个社会压力事件中,婚姻、工作中的烦恼、被拘留、配偶死亡、睡眠习惯的主要变化、亲密家庭成员的去世是居于前六位的压力事件(Holmes & Minoru, 1973)。罕见病儿童家庭因为儿童所患疾病的特殊,其家庭面临的压力与一般家庭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截至2014年9月30日,以“罕见病”为关键词,在“读秀”学术搜索与全文递送系统中查找到的学术论文共有1675篇,其中医药卫生方面为1418篇,占到85%;其他的就是一些科普宣传、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工业技术、农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一共为124篇,占到7%,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一共14篇,占不到1%。在为数不多的这些社会科学研究中,多数为政策性的文章,一共有10篇。没有一篇是针对罕见病儿童家庭压力和应对、抗逆力的文章。
中国港台地区文献中,截至2014年10月25日,讨论罕见病患者与家庭压力或困境的研究文章共有11篇,以下的文献主要是建立在对外国文献和中国港台文献阅读和整理基础上的。蔡孟芬认为罕见病家庭面对疾病所承受的冲击和压力,超出一个家庭所能负荷的范围(蔡孟芬,2006)。中国台湾学者陈志升指出,由于罕见病患者人数稀少,所需要的医疗技术与药品的研发需要耗费许多的金钱与人力,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医界与药商都缺乏研发与制造的意愿,因为即使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只能帮助到极少数的病患,根本无利可图;相比治疗一般病患,医院与医师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换来的却是不成比例的回报。因此,无论医院还是医生,大多不愿投入精力对罕见病患者进行治疗,从而使他们成为医界孤儿,进而造成罕见病患者的医疗需求不能得到满足(陈志升,2000)。
罕见病儿童家庭传统上很少受到来自卫生当局、临床和研究领域的关注。但具体有什么样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尚没有系统的研究。Matilda Anderson等人通过对46个家庭的调查,认为照顾遗传代谢疾病儿童的澳大利亚家庭会受到以下几个不利因素的影响:耽误诊断、缺乏同辈支持、缺少心理支持(Matilda Anderson et al., 2013)。从现有文献来看,我国对罕见病儿童家庭的现状研究很少,尚没有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全面调查研究(尚晓援,2011)。
罕见病患者依照不同的发病年龄、病情轻重、预期寿命、治疗时机、经济条件等因素,可能有外观、行动、代谢功能、成长发育、器官组织、智能等多方面的异常状况,并衍生出患者及家属衣、食、住、行、养育等生活适应问题;加上长期巨大的金钱、时间支出和精力消耗,必然给个人、家庭和社会等带来角色调整的冲击及无法承受的沉重压力。其中有些罕见病更是因为其遗传性,家族兄弟姐妹或子女罹患同样病症,加上所需的医疗资源短缺,所以严重影响生活品质乃至寿命长短,其相关问题涵盖了生理、心理、心灵、家庭、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吴庶深,2006)。
一 罕见病儿童的家庭压力
详细来说,罕见病儿童的家庭压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庭系统的失衡。在家庭系统中,家庭是一个互动的整体,一个完整的家庭往往可以维持整个家庭的平稳运作,如此才不易让生活在此情境内的家庭成员在心理上产生困扰。而个人的问题可能是家庭失去平衡造成的结果,也可能是家庭失衡的原因,个人和家庭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谢秀芬,1989)。Bischoff等表示,家庭中任何一个成员有困难,都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困扰;家庭中诞生了有身心障碍的孩子,这对整个家族及每个家庭成员,都会产生极大的冲击(转引自詹珮宜,2000)。Buscaglia也认为,障碍不仅导致个体本身及其家人的痛苦、泪水、羞耻、矛盾,特殊儿童的家人还得直接承受此煎熬,他们要比一般正常儿童的家人面临的挑战会更棘手(转引自黄秋霞,2002)。
第二,罕见病儿童对父母的影响。一个家庭有了特殊幼儿所引起的痛苦、哀伤、落泪、迷惘,以及因经济困乏而陷入困境,是一般家庭所无法体会的,而父母要更直接承担这种困苦(王大延,1995)。生育先天性缺陷儿童会给家庭成员带来某些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母亲的影响远大于对父亲的影响(Timko & Moos,1992)。这种影响包括母亲的人生观、夫妻关系、家庭生活、经济状况、工作及人际关系。这种影响甚至会波及整个家庭,整个家庭需重新调整(黄琏华,1995)。因为传统上母亲更多待在家里,被认为比父亲有更多的照顾责任,特别是当孩子有特殊需要的时候(Konstantareas et al.,199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母亲离开家庭进入职场。如果母亲有工作,父亲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孩子交流,承担更多照顾孩子的职责(Barnett&Baruch,1987)。因此,罕见病儿童的出生,也必为其家庭及母亲带来某种程度的困扰。由于身心障碍儿童本身的特质因素,加上多数父母缺乏养育照护的知识和技巧,因而罕见病对主要照顾者的影响是长期、非预期的,其中以母亲在此种家庭中的牺牲及受害为最大(周月清,1998)。有学者指出,家庭会在家庭成员因疾病突然死亡前经历一连串的压力源,包括照顾时间增加、因医疗费用与失去工作而发生经济问题、情绪透支、工作与家庭规律受干扰、社会孤立感、丧失个人时间或与家人相处时间(Patrick et al., 2004)。而罕见病儿童患者因特殊身心特质需长时间的特殊照护,这将会给家庭带来很大冲击,尤其对主要照顾者——母亲更是一大打击,母亲会因此产生家庭及身心方面的调适问题。因此,家庭成员当获知家有罕见病儿童患者的确凿事实时,都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创伤,但研究也表明,与母亲相比,父亲更难接受孩子有先天精神性疾病(Price-Bonham et al., 1978)或身体残障(Tavormina et al., 1981)。
第三,家庭在应对压力方面的研究。早期关于家庭压力和应对的模型提出由于儿童残障带来的家庭压力受家庭生态资源的影响,包括社会支持的可获得性(Minnes, 1988)、积极的家庭功能(Minnes, 1988)乃至父母双方的生活满意度、对儿童身患疾病的调整程度等(Milgram & Atzil, 1988)。更为重要的是,有研究发现父亲的精神健康状况不仅和自己有关,而且还与妻子对养育一个残障儿童的困难的理解和认知有关(Nagy & Ungerer, 1990)。因此,父母的压力状况不仅和他们自身有关而且还和他们的配偶对家庭生态资源的评价有关。
陈亭华(2002)指出,罕见病儿童家庭主要的压力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医疗诊断治疗、康复、医疗照护知识、疾病严重程度、医疗药品取得、康复就近性、经济安全、社会能见度、压力团体动员能力等方面。上述种种因素交互影响,更使得罕见病儿童家庭可能缺乏这些社会资源的资讯或获得的资讯不足而丧失应有的权益,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个案家庭,如农村罕见病家庭和城市低收入罕见病家庭。社会对罕见病儿童家庭遭遇到的困境所知有限,从而忽略了罕见病儿童及其照顾者的真正需求。
总体来说,罕见病儿童家庭面临的困境有:①医疗不确定性,罕见病儿童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与照护,延误控制病情的时机,因而使本来可以避免的罕见病无法避免;②经济安全问题,罕见病儿童的治疗和康复成本非一般家庭所能负担,因而造成其家庭的经济压力;③社会资源不足,由于社会缺乏对罕见病有关知识的了解,无法正视罕见病儿童及其家庭的困境与需求,长期以来,罕见病儿童及其家庭,在上述困境的彼此交互影响下,深化了其自身因罕见病所导致的困境,从而成了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二 影响罕见病儿童家庭压力的因素
综合各相关照顾罕见病患儿的文献,影响家庭压力的因素可归纳为疾病本身、病童状况、家庭生活及社会四项主要的压力。
(一)疾病本身
罕见病本身既是对医疗卫生界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更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
Remco L. A. de Vrueh认为,促进罕见病药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加入这一场针对罕见病的战斗中,特别是需要中国、印度、土耳其这些国家的加入,只有这些国家也加入,才能真正形成全球范围内的针对罕见病的战斗(Remco L. A. de Vrueh, 2013)。Simoens认为需要一个更透明和更科学的孤儿药的定价机制和赔偿标准。罕见病带来的真正的负担难以估计,因为对于大部分罕见病,流行病学数据是缺乏的或不足的(Schieppati et al., 2008)。罕见病可能由并不熟悉此病的医生诊断,而目前尚缺乏有关医生在这个病人群体中的角色研究(Knight & Senior, 2006)。
对罕见病家庭而言,疾病本身就是一项长期的压力。罕见病很难诊断、处遇,缺乏适切的公共卫生服务,缺乏有经验的卫生专家及有效的治疗方案(Zurynski et al., 2008)。许多罕见病是慢性复杂性疾病,常常伴随着身体的、智力的以及神经方面的病变,再加上缺乏同辈群体和社区支持服务,因此,对病人及家庭而言,心理的社会的和情感的影响就显得非常重要(Kole & Faurisson, 2009)。罕见病所造成的饮食上的限制,药物使用后的负面影响及无药可治的现实,给罕见病家庭造成很大的压力。事实上,长期病患者,对家庭本身就是一个压力源,不论其病情是否恶化或稳定,也不论发病年龄大小,皆会对家庭造成压力。罕见病通常是较严重的疾病,有的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且治疗都是终生的,每种疾病的严重程度不一样,也没办法预测将来的状况,因为病童随时会病逝,被诊断的病因常不明确,检查的时间很长,自婴幼儿期就已经患病;他们开始接受漫无止境的检查、追踪、治疗,服药、打针,甚至开刀,做各种实验性的治疗(唐先梅、李淑娟,2002)。
具体来说,对于许多罕见疾病患儿而言,“吃”意味着关乎生命的重重限制。他们能吃的食物种类非常有限,且经常还需要限制数量或改变食用方法,例如,患肝糖原贮积症的病童必须将“生的玉米粉”用水泡开来食用以维持稳定的血糖;患白胺酸代谢异常症的病童,多半要被限制蛋白质的摄取,以避免无法代谢掉的有毒物堆积,否则可能损害智力、影响生长发育,甚至死亡。因此,如何兼顾营养、美味及材料上的多方限制,对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病童母亲,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罕见疾病还有重度、轻度之分,饮食形态及分量也有区分,吃饭及吃玉米粉的时间也须把握,所以这些常常会造成父母及病童双方面的紧张。类似的长期压力,会让病童情绪不稳定,特别是在饮食上的特殊要求,使别人可以吃的东西,罕见病儿童却不可以吃。但好奇心促使病童偷偷去碰,或者受同龄人的影响,病童希望自己与一般人无异,所以他们会尽量跟同学做一样的事情(唐先梅、李淑娟,2002)。饮食上与同龄人的不同,在外吃饭的不便,病童遭受到另眼相看等种种问题,可能会造成病童心理发展上的困扰,也造成照顾者的担心与压力。
另一个对罕见病家庭压力有很大影响的因素是药物。由于科研或市场的限制,有些用于治疗罕见病的药物尚未研发或不能在市场上买到。这就导致很多用于罕见疾病的药物不是用来专门治疗该项疾病的,服用这样的药物只能使病情较为缓和或稳定,且许多药物不易获得或相当昂贵,这给病患家庭造成很大压力。此外,药物所造成的后遗症或并发症也成为此类家庭的新压力。有些疾病目前没有药,但是可以用实验的性质让患童试用某一种药,不过实验的结果却无法完全得知,很多药物都有副作用。例如,长期吃特殊奶粉会使病童缺乏某些蛋白质,影响到神经发育,所以须做一些配合治疗且须定期会诊;而口服排铁剂、人体试验的结果会造成肝硬化,甚至危害到生命。因此,只能早发现、早控制,以延缓器官损坏的程度,若等到肝脏已经没办法负担,坏掉了,则唯一的医疗方法就是肝脏移植;如果移植之前其他的器官(如肾脏)坏掉或是其他器官坏到一定程度的话,则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
(二)病童身体状况
黄琏华对51个生育先天性缺陷儿家庭的研究显示,小孩外观越有明显的缺陷,母亲越不愿主动向他人提起小孩的状况或带小孩出门,缺陷的程度越严重,母亲的情绪反应越大,对母亲的影响也越大。罕见病所造成的外观的特殊状况会影响其家人在面对此疾病时的反应(黄琏华,1995)。此外疾病所造成的孩子身体状况亦是造成家庭压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孩子的身体结构、身体功能、身体感觉及造成缺陷的原因(程子芸,1991)。病童为男性,开刀次数越多,母亲的压力越大。发病越迟缓者,其母亲的压力越大(程子芸、陈月枝,1998)。此外,对孩子未来的不确定性亦是许多母亲共同的压力。由于此类孩子的预期寿命可能较短,父母在面对子女的未来时皆有较大的压力感受(唐先梅、李淑娟,2002)。
(三)家庭因素
1.照顾知识的缺乏
由于许多罕见病病童人口不多,因而相关的资料及照顾资源缺乏,这使得照顾者在照顾此类疾病的子女时有很大的压力。潘依琳等指出疾病的实际原因有时医师也不清楚,加上有关疾病的资料有限,照顾者往往不知道如何发现病人的病情变化,不知道照顾时应注意的事项(潘依琳等,1998)。当病童在被照顾时患有并发症,需与母亲分离接受治疗或有喂食困难,常会使母亲感到照顾上的挫折,并评价为自己能力不足(程子芸,1994)。
2.时间及精力的不足
主要表现为照顾者尤其是母亲所感受到的压力,包括:角色疲乏、角色紧张、角色负担过度、角色严重冲突,情绪上紧张、疲惫、无力感、沮丧等。当家中有一名长期需要照顾的病童时,女性往往成为照顾者的第一人选,同样在家中有罕见病病童时,母亲往往也就成为照顾上的不二人选。也由于母亲通常是病童的主要照顾者,家庭疾病在疾病照顾上的重要性,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医疗保健制度上都应重视家庭的影响力,要把家庭视为健康照顾的基本单位。在家庭层次,95%以上的疾病照顾由同住家人完成,核心家庭较缺乏人力资源,年轻成人是提供照顾的主力,其中的妇女,特别是职业妇女,往往有更重的负担。母亲在孩童照顾中扮演主要照顾者的角色(黄琏华,1995;赵明玲等,1998),许多母亲因而辞去工作专心照顾生病的子女(唐先梅、李淑娟,2002)。亦有父亲作为病童的主要照顾者(赵明玲、高淑芬,1997),但比例较低。
持续照顾病人的过程是对个人资源的消耗,而当照顾者的角色只落在病人身上,全部的个人活动都围绕着单一角色(照顾者)会使照顾者产生角色疲乏(罗静心,1992)。照顾者常发生角色紧张、角色负担过度或角色严重冲突等情形。虽然父亲和母亲都有压力,但生育先天性缺陷儿对母亲的影响似乎大于对父亲的影响(黄琏华,1995)。在中国比较传统的家庭,观念比较保守,只要生出缺陷小孩,人们都是责怪女方,在传宗接代的观念上,亟需一个健康正常的男婴来传递香火,而主要承担生育任务的女人就变成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甚至被诅咒、被排斥的人,因此母亲往往承受很大的压力(唐先梅、李淑梅,2002)。由于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替代母亲的角色,加之母亲本身情绪会随着病童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当病童生理状况变得不稳定时,母亲也会产生生理上的不适(如腹泻、头痛等)或精神上的疲乏、失眠,情绪上的压力,母亲本身情绪无法疏解(黄琏华,1995;陈姝蓉、黄美智,1999)。更由于社会活动的限制,加上照顾者生理、心理、社会及经济上的冲击,而产生一个具有很大压力的环境,特别是情绪上紧张、疲溃、无力、沮丧等,这在女性照顾者表现得尤其明显。家属在自感健康状况较差时,压力感会较大。如母亲有身体或精神方面的问题,或原先有对怀孕及生产的负向态度与看法,或不愉快的生产经验使之无法投入对婴儿之照顾,母亲的负向自我观念也会使她缺乏自信,认为自己没有照顾或养育孩子的能力(程子芸、陈月枝,1998)。
3.经济压力
对于罕见病儿童家庭而言,经济压力也是很重要的压力(Matilda Anderson et al., 2013)。经济压力主要来自手术费用、托儿费、交通费、教育费、康复费用、特殊器材费用以及父母因为要带病童做检查和治疗的费用及照顾儿童而无法工作带来的压力。由于许多特殊儿童患有先天生理上的罕见病,需要经过数次手术或长期依赖医疗系统来维持,长期下来就是一笔可观的费用,儿童年纪还小者,常需要双亲之一或聘请专人照顾或被寄养在特殊机构,定期再被接回家,这笔“托儿费”核算下来,常占家庭收入的1/4~1/3,等到孩子上学后,交通费、教育费和其他仍固定支出的复健医疗费或特殊器材费等,便足以成为一个家庭的沉重负担(周欣颖,1993)。黄琏华在研究“养育唐氏症儿的家庭冲击”时发现社会福利不健全,庞大的医疗费用困扰了大部分唐氏综合征患儿的父母,但却只有16.4%的家庭申请通过了政府的补助。即使在中国台湾有全民医保的情况下(医疗费用大多由政府给付),罕见病儿童家庭的经济压力依然很大(黄琏华,1995)。因为主要照顾者常常要带病童做检查及治疗,以致无法工作,特别是当家中还有其他小孩要抚养时,其家庭经济压力会更大(梁蕙芳、骆丽华,1999)。
孤儿药的费用和照顾费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在欧洲,每年每个罕见病儿童花在现存的孤儿药方面的费用在1251~407631欧元,中位数为32242欧元(Schey&Hutchings, 2011)。在中国台湾,就台北地区的调查数据而言,使用机构式照顾的病患,家庭平均负担35269元的费用支出。而台北地区家庭照顾的病患中,轻度病患的家庭照顾费用平均只需23630元,因此学者建议轻度失智的病患适合在家庭被照顾。至于中度失智病患,家庭照顾支出平均为47364元,重度及以上病患,其平均的家庭照顾成本达67096元(陈春闳,1998)。
有些罕见疾病并没有被纳入医疗报销的范围,这就意味着这笔巨大的支出全部压在家庭身上,当病人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时常常遭到拒绝。同样一种疾病,却表现在身体很多不同的部位,需要到不同科室诊疗,这增加了人力、物力及经济的成本。再加上药品及很多检查费用都要自费,经济压力巨大。有的患儿几乎每个月都要住院一两个星期,有的家庭常需要长途跋涉去做治疗,医疗费用加上来回车费、三餐使支出巨大,而且时间及体力的消耗惊人。因为患儿常有其他的并发症,因此即便在家中照顾,家里也必须购买治疗的器材如注射用具、呼吸器等,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家庭只靠一份收入维持,遇到经济形势不好,往往还要担心工作不保,进而影响到患童的治疗(唐先梅、李淑梅,2002),这些现象更使得家中有罕见病患者的家庭有较大的经济压力。
4.家庭关系的改变
首先,夫妻关系是罕见病儿童家庭中最先受到影响的。梁蕙芳等提出,夫妻如果在儿童患病期间不能同心共渡家庭的危机而只有相互责备对方,夫妻间的矛盾将大大增加,夫妻关系的危机将明显加深。有的病童父亲在孩子患病期间有外遇。再加上民间传统观念,对患病原因认知的压力、社会隔离的压力、医疗经验不佳等往往也相伴而来(梁蕙芳、骆丽华,1999)。此外,生下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往往需要立即分离治疗或手术,经济压力随之而来,父母亲须有可能会失去孩子的心理准备等,这些相伴因素足以使家庭陷入婚姻关系高危险的情境之中。特别是,如果医生告知该疾病是遗传性基因导致的,且该基因是遗传自母亲的话,大都会引起双方面的压力,造成很多夫妻分居或离婚。也有的为了生个男孩而发生婚外同居乃至重婚等现象,有的夫妻虽未离婚但妻子每天都要去面对孩子的疾病,在还没办法接受这一事实时,再加上大夫早出晚归,常会有不安全感,进而造成婚姻危机(唐先梅、李淑娟,2002)。
其次,病童照顾者所接触的环境给家庭带来压力。照顾者周遭所接触的人,包括病童、病童兄弟姐妹、配偶亲戚朋友等,他们所说的话、所表现的行为、所遭遇的状况,都有可能给照顾者造成压力(叶明莉,1994)。其中父亲的态度对母亲产生重大影响,其态度越正向越能参与照顾缺陷儿的工作,对家庭的稳定越有帮助(黄琏华,1995)。越缺乏正向支持系统,尤其是父亲的态度和投入程度不佳时,越会影响母亲的感受(程子芸、陈月枝,1998)。
还有些因素,如其他家人的态度、医护人员的态度和医护人员的沟通等也会影响母亲对缺陷儿的感受及态度,生育先天性缺陷儿对父亲也同样会造成影响,但对母亲的影响大于对父亲的影响,其他家人,包括兄弟姐妹及(外)祖父母,也不可避免地有哀伤及情绪反应(黄琏华,1992)。一般而言,姐姐会暂代母亲的角色去照顾罕见病弟妹,让母亲有喘息机会(吴慧英,1995)。而兄弟姐妹之间也有可能因母亲花太多时间和精力照顾病童而造成正常子女的抱怨与不满(唐先梅、李淑娟,2002)。
(四)社会因素
1.社会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带来的压力包括“异样的眼光及不适当的关心”。“异样的眼光及不适当的关心”指一般社会人士对患儿的疑问以及文化信念。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对于罕见病儿童生病的原因多有揣测或穿凿附会的说法,这方面的耳语或异样眼光常给照顾者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林芳怡,1996)。有的罕见疾病患儿因为身体、脸上有很多的病变,这致使外观特殊,所以常会招来外人的异样眼光及言语。这种无止境的、24小时陪伴的压力,对母亲而言是一种刺痛(唐先梅、李淑娟,2002)。
2.就医
医疗过程,包括医疗措施(如手术及各种检查、治疗、照护),手术对孩子的威胁,以及病愈后医疗环境、医疗时间等皆会对病患家庭造成很大的影响(程子芸,1994)。在家庭对疾病的反应过程中,诊断初期是家庭成员最难接受的时期,尤其是面对那些需长期照顾的病童(黄琏华,1994;程子芸,1994;林芳怡,1996;于素珍等,1998)。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会带来诊治、早期疗育乃至康复的艰难。因为大部分医疗院所都集中在大城市中,全国遗传疾病类医师数目有限,经验也不足,再加上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早期疗育中心等机构更是稀缺,所以非都会区特别是农村的病患家庭会感到相当不便,不论是疗育中心,还是康复中心,都存在城乡及地区的差异。这也往往造成许多乡村的病患及家属经常要长途奔波,有一些罕见病儿童在发病的时候去医院做检查,等到每一科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才被送到比较大的医院,然后在大的医院各个科室转一圈做完检查之后依旧找不到原因时,才被送到遗传科,等到遗传学诊断出来,病童都已经病得非常厉害了。
罕见病特殊的病情及治疗会带给医生特殊的角色。因为医生面对的也是无法预知的病情及治疗,但因为他在病童医疗的过程中要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又必须给家属及病患解释病情及提供心理支持,同时还要让家属及病童学会面对事实。经常的情况下,如果疾病是与性别相关的遗传病,医生往往会先观察这个家庭成员的互动,如果互动不是很好,会暂时隐瞒事实或想办法用比较婉转的方法来说明。医生也扮演提供信息的角色,他要提供医疗照护患病童的相关资讯给护理师、药师、复健师、社工师甚至政府及媒体等,责任重大,影响的层面也很广泛(唐先梅、李淑娟,2002)。
3.就学
就学包括罕见病儿童本身的就学和针对罕见病儿童家庭开展的家庭教育。对于包括罕见病儿童在内的特殊儿童教育而言,实施融合教育,回归主流是特殊教育思潮的主流,目的在于使身心障碍学生由特殊学校或特殊班走入一般学校或普通班。但是这个理想和目标目前却流于形式和口号,甚至引起标签效应而造成反效果。或者即使实施了,却因学校或老师的偏见而不能接纳这类孩子。而且由于身心障碍特殊儿童教材的特殊性,必须依据学生的差异性由专业教师编教材,但因教师的专业能力不足以及不了解学生的个别需求,或因教师流动率高而造成个别化教育方案不能衔接。此外很多特殊班级教师兼其他行政工作,因而未能有效致力于教材的研究与编写。
由于特殊教养机构不足,很多病童已经排了两年多还找不到合适的特殊教育学校或教养机构(林芳怡,1996)。有些罕见疾病患儿的疾病常是渐进式的,时常要住院一段时间,所以病童要比一般的儿童面对更多的压力,他们只剩下一小部分时间学习,有一些儿童即使很喜欢学习,也需要比一般儿童付出更多的辛苦和代价才能达到和其他儿童一样的学习成绩。这个时候如果老师或者同学没给他一个适度合理的评价,对他而言会是一个不小的挫折。对他而言,这意味着对抗疾病的努力没有得到承认性的回馈和鼓励。此外,有些幼儿园不敢接收病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疾病不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知如何照顾,怕惹麻烦。没有适合的教育系统往往造成许多罕见病儿童因未进入教育系统而被排斥。部分进入教育系统的病童,也担心会被同辈群体排斥,或不能被大家接受,因此会出现一些反叛行为(唐先梅、李淑梅,2002)。
也有研究认为,针对罕见病儿童家庭开展家庭教育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教育可以让病童和家庭知道他们有哪些合法的权利,使父母知道如何应对儿童的问题行为和如何与儿童交流(Bernstein & Barta, 1988)。研究显示为父母提供的关于儿童教育方面的咨询信息能减轻父母的担心和压力,帮助他们调整(Aksaz, 1992)。教育内容方面,家长希望得到一些关于如何应对儿童行为以及他们的孩子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等信息(Kendall, 1998),他们希望得到有关行为管理、教育技能和一些能在家里实际用得到的服务和资源等,包括有关特殊教育项目和既有课程之间的对比、一些针对个人的教育计划等(Berger, 2008)。对残障儿童开展的一些项目显示,通过支持家庭提供家庭需要的知识和信心等的家庭介入对儿童成长的帮助很大,特别有利于处理儿童的一些行为问题和学习问题,减少交流障碍(Cavkaytar et al., 2012: 111)。
4.就业
由于针对残障人士的福利政策与法律的缺失或执行不力,在实际生活中,残障者要获得一个职位并非易事,其中智障者更是受到差别对待(黄琏华,1994)。目前有关残障人士的福利法虽然规定各级机构需聘用一定比例的残障人士,但并未规定一定是罕见病人士,而且这一政策在实际中并未完全落实,这导致许多罕见病儿童的父母为其子女的未来感到忧心及压力。
对于其他组织如民营企业雇用罕见病者的态度方面,调查结果显示,雇主对罕见病者就业仍有刻板印象存在,肢体罕见病患者的就业机会最多,视觉障碍、智能不足、自闭症与多重障碍者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而罕见疾病的身心障碍者多属于多重障碍者,因此其就业就更加困难。
罕见病患者在就学、就业的过程中,均面临相当不友善的环境,这使得罕见病患者自儿童时期到成年就业各阶段均蒙受社会种种歧视与排斥,这对罕见病患者心理、生理健康发展都构成极大伤害,也影响他们未来能接受完整教育以拥有自力更生的机会(曾敏杰、杜孟霖,2002)。唐先梅等的研究发现,有的机构或老板知道是疾病患者,就不想雇用,虽然其中部分机构人事部门或老板对疾病患者表示理解,但大部分不愿继续雇用,如海洋性贫血患者因为固定每三个星期就要去输血,一次需要约10到15个小时,所以需请假一天,再加上其他一些检查,一个月最少需要请假三四天,所以相对而言,他的工作时间就缩短了。在中国台湾,各个县市都有身心障碍者就业基金,根据身心障碍者保护法,公家单位员工满50名,就要聘一个身心障碍者,聘不到足够的人数就会被罚,很多公司宁愿被罚,也不愿聘用残障人士。这就是罕见病儿童父母对其未来就业不抱太大希望的原因之一(唐先梅、李淑娟,2002)。学者叶秀珍认为,就罕见病患者的个人尊严以及长期社会成本而言,除了要确保罕见病患者的生存机会(疾病治疗与控制)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协助其未来能自力更生而不必依赖社会救助体系维生,因此罕见病患者受教育权与就业权的保障便非常重要(叶秀珍等,2002)。
5.就养和临终关怀
“就养”在《辞海》中的定义为“接受奉养”。这里的“就养”主要指在家庭和就养机构进行的医疗和护理伺候、照顾饮食起居。
临终关怀(hospitalpice)指对生存时间有限(6个月或更少)的患者进行灵性关怀,并辅以适当的医院或家庭的医疗及护理,以减轻其疾病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孟宪武,2002: 23)。就养和临终关怀对许多重病的罕见病病童,尤其是晚期、末期的病童而言有其必要性。一般罕见病病童在饮食上要注意,甚至药物的内容、药物的调配和食用、服用的时间都要注意,还有很多居家治疗、康复的事情需要注意,所以可以以到宅服务的方式解决,但一些病童在末期治疗时需要大量的医疗设施,于是就养机构就显现出相当的必要性。然而目前国内针对这些病童及家属的空间安排及医疗设施则是有限的。故罕见病患者的问题不仅在于医疗方面,还必须有就学、就业与安养等社会福利服务加以配合(吴明烨,2002)。
概而言之,家中遭遇儿童身患罕见病会对家庭中父母及家庭系统造成多重压力——家庭系统的失衡及父母心理创伤和挣扎等。其影响因素包括罕见病本身的“缺医少药”状态、疾病对病童身体机能的影响、病童吃药过程中的各种艰难、对饮食的限制;缺乏照顾知识,时间、精力负荷过重,照顾人手不足,经济压力巨大,家庭关系的改变,社会价值观和就学、就业、就养过程中各种制度及文化带来的社会排斥等。对于罕见病儿童家庭困境和风险性的研究,应该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病童家庭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以增进对罕见病儿童家庭现状和各方面额外需求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