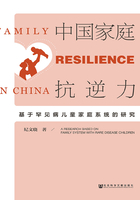
第二节 概念界定
一 “罕见病”定义
罕见病是从患病率角度归纳出的一个彼此之间没有关联的疾病群,包括数千种不同原因的、发病率较低的疾病。虽然罕见病发病率很低,涉及的个体数量有限(欧盟标准每2000人中不超过1例,美国标准每1250人中不超过1例),但因为满足这些标准的疾病种类数量巨大(据统计,美国目前有7000多种罕见病,且每年新增十几种罕见病,占到人类疾病总数的10%),因此,受罕见病影响的人为数众多。据估计,这一数字在欧洲可能为3000万,在美国可能为2500万,在我国,按照发病率(新生儿发病率)为1/10000或患病率为1/500000的标准来计算,目前估计有1000万~2000万病例 (复旦大学出生缺陷研究中心马瑞教授等人在2011年按照患病率为1/500000推算我国罕见病患者有1680万人),全球罕见或极罕见病患者总数约为3.5亿人
(复旦大学出生缺陷研究中心马瑞教授等人在2011年按照患病率为1/500000推算我国罕见病患者有1680万人),全球罕见或极罕见病患者总数约为3.5亿人 。之所以出现这种统计数据上的不确切性,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根据其法律和政策对罕见病的认定标准有所不同:有的是根据患病人数的多少,有的则除了患病人数的多少,还加入了其他的认定标准,如疾病的严重程度、是否存在足够的治疗手段等。罕见病,在欧洲指患病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低于1/2000的疾病(Kole &Faurisson, 2009),在美国指患病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低于1/1250的威胁生命或慢性衰竭性的疾病或病变(Remuzzi & Garattini, 2008)。日本“孤儿药法”则将罕见病界定为疾病人数少于50000人者。中国台湾2006年经卫生署罕见疾病委员会通过的罕见病一共有129种,其认定标准为“罕见性”、“遗传性”以及“诊疗困难性”三项指标
。之所以出现这种统计数据上的不确切性,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根据其法律和政策对罕见病的认定标准有所不同:有的是根据患病人数的多少,有的则除了患病人数的多少,还加入了其他的认定标准,如疾病的严重程度、是否存在足够的治疗手段等。罕见病,在欧洲指患病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低于1/2000的疾病(Kole &Faurisson, 2009),在美国指患病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低于1/1250的威胁生命或慢性衰竭性的疾病或病变(Remuzzi & Garattini, 2008)。日本“孤儿药法”则将罕见病界定为疾病人数少于50000人者。中国台湾2006年经卫生署罕见疾病委员会通过的罕见病一共有129种,其认定标准为“罕见性”、“遗传性”以及“诊疗困难性”三项指标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罕见病的定义见表1 -1)。但我国目前并没有对罕见病范围进行界定的政策,没有统一的界定意味着罕见病很难作为一个专用名词进入政策视野,针对罕见病中各种疾病的规定目前只散见于各地政策中。“依据WHO对罕见病的界定标准和国内外的疾病发病率,我国确定的11种罕见病,分别为脊柱裂(神经管畸形)、新生儿溶血症、百日咳、流行性乙型脑炎、斑疹伤寒以及血吸虫病等。”(龚时薇等,2011)黄尚志的研究认为,如果以发病率为判断标准,在中国难以回答哪些疾病是罕见病,因为除了地中海贫血和苯丙酮尿症外,我国基本没有本土发病率的数据,也从来没有投入经费进行遗传病发病率的调查,临床上尚无遗传病的登记制度(黄尚志,2010)。如果把罕见病定义为发病率极低的疾病,那么在中国,它包含了多种类型。依发病年龄可分为早发型(出生至儿童期即发病)与晚发型(青春期后才发病),大家较为熟知的早发型罕见疾病包括:黏多糖症(黏宝宝)、成骨不全症(玻璃娃娃)、重症β -海洋性贫血等;晚发型罕见疾病则包括:三好氏远端肌肉病变、亨丁顿舞蹈症、脊髓性小脑萎缩症(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企鹅家族)等(吴庶深,2006)。2010年5月17日,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学分会专家会议,对中国罕见病定义达成共识: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参照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及周边国家如日本等的罕见病发病率,将罕见病定义为患病率低于1/500000的疾病;在新生儿中发病率低于1/10000的遗传病可定义为罕见遗传病(魏珉、张瑞丽、赵志刚,2010: 48~50)。罕见病发展中心将罕见病定义为患病率低于1/100000或在新生儿中发病率低于1/10000的疾病。由于在对罕见病界定方面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国家又没有明确的政策文本,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是罕见病发展中心的这一定义(具体的罕见病范围见表1-1)。此定义下的罕见病儿童也将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罕见病患者中约50%的是儿童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罕见病的定义见表1 -1)。但我国目前并没有对罕见病范围进行界定的政策,没有统一的界定意味着罕见病很难作为一个专用名词进入政策视野,针对罕见病中各种疾病的规定目前只散见于各地政策中。“依据WHO对罕见病的界定标准和国内外的疾病发病率,我国确定的11种罕见病,分别为脊柱裂(神经管畸形)、新生儿溶血症、百日咳、流行性乙型脑炎、斑疹伤寒以及血吸虫病等。”(龚时薇等,2011)黄尚志的研究认为,如果以发病率为判断标准,在中国难以回答哪些疾病是罕见病,因为除了地中海贫血和苯丙酮尿症外,我国基本没有本土发病率的数据,也从来没有投入经费进行遗传病发病率的调查,临床上尚无遗传病的登记制度(黄尚志,2010)。如果把罕见病定义为发病率极低的疾病,那么在中国,它包含了多种类型。依发病年龄可分为早发型(出生至儿童期即发病)与晚发型(青春期后才发病),大家较为熟知的早发型罕见疾病包括:黏多糖症(黏宝宝)、成骨不全症(玻璃娃娃)、重症β -海洋性贫血等;晚发型罕见疾病则包括:三好氏远端肌肉病变、亨丁顿舞蹈症、脊髓性小脑萎缩症(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企鹅家族)等(吴庶深,2006)。2010年5月17日,中华医学会医学遗传学分会专家会议,对中国罕见病定义达成共识: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参照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及周边国家如日本等的罕见病发病率,将罕见病定义为患病率低于1/500000的疾病;在新生儿中发病率低于1/10000的遗传病可定义为罕见遗传病(魏珉、张瑞丽、赵志刚,2010: 48~50)。罕见病发展中心将罕见病定义为患病率低于1/100000或在新生儿中发病率低于1/10000的疾病。由于在对罕见病界定方面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国家又没有明确的政策文本,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是罕见病发展中心的这一定义(具体的罕见病范围见表1-1)。此定义下的罕见病儿童也将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罕见病患者中约50%的是儿童 。
。
罕见病既是对医疗卫生界的一个挑战,又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罕见病由基因突变引起,对这些疾病的研究有助于破解基因这一生命的密码。医学文献显示人体约有10万个基因,每个人的基因中平均约有7组到10组基因存在缺陷,一旦父母双方存在相同的缺陷基因,孩子就有可能患上罕见病。可以说,有生命传承的地方就有发生罕见病的可能。一旦罹患罕见病,儿童及家庭都将面临健康、成长乃至生命威胁,几乎终其一生都承受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因此罕见病也是任何一个生命都要面对的可能的风险。这些疾病普遍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案,即便在医疗技术较为发达的美国,目前也只有不到5%的罕见病是有治疗方案的。因此,罕见病在给个体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压力的同时也给社会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政策、社会工作服务等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对罕见病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医学和社会问题(Schieppati et al., 2008: 2039-2041)。
目前对罕见病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专门的针对罕见病定义、药品开发支持等方面的政策(见表1-1)。究其原因,除了各国政府的努力外,这些国家和地区与罕见病相关的政策的出台也离不开各个患者组织的积极参与,他们在推动政策的出台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表1-1 罕见病认定标准、定义及孤儿药政策法规

资料来源:Pedro Franco, 2013。
二 家庭和罕见病儿童家庭
现实社会中的家庭存在形式多种多样,很难做出统一的定义。《康熙字典》所录《说文》对“家”的解释为:“豕居之圈曰家,故从宀从豕,后人借为室家之意。”而“庭”则指“厅堂”,为“正房前的空地”。《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认为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孙本文认为:“家庭是指夫妇子女等亲属所结合的团体。家庭成立的条件有三:第一,亲属的结合;第二,包括两代或两代以上的亲属;第三,有比较永久的共同生活。”(孙本文,1945: 51)中国台湾学者谢秀芬认为:“家庭的成立乃是基于婚姻、血缘和收养三种关系所构成,在相同的屋檐下共同生活,彼此互动,是意识、情感交流与互助的整合体。”(谢秀芬,1998: 73)美国社会学家古德(Goode)认为家庭包含了下列五种情况中的大多数:第一,至少有两个不同性别的成年人住在一起;第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分工;第三,他们进行许多经济与社会交换;第四,他们共享许多事物,如吃饭、性生活、居住;第五,成年人与其子女间有着亲子关系,父母对孩子都拥有某种权威,但同时也对孩子负有保护与抚育的义务,父母与子女相依为命;孩子之间存在着兄弟姐妹关系,共同分担义务,相互保护并且相互帮助(转引自彭怀真,1996: 169)。也有学者认为家庭最基本的特点是由具有亲属关系的人们构成的集团,家庭就是以夫妇、亲子、兄弟等少数近亲者为主要成员,由成员间深厚的相互感情联系结成的、最初的社会福利集团(望月嵩,2002: 83)。
贝克认为中国的家庭概念具有更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Baker, 1979)。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家庭的概念是不同的。英文中的“family”表示的是由夫妇和未婚子女所构成的集团,而中国的“家”往往包括了已婚成年子女和其他亲属,有时甚至还包括仆佣等。为了表示这种差别,他特别提出把中文的“家”译为英文的“expanded family”(Fei, 1933)。在中国,“家,是个伸缩性极强的概念,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这种模糊性正是汉族家的重要特征。它可以扩展到社会和国家,作为一种具体结构表现在姓、宗族和家庭与家户上(麻国庆,1999: 1~3)。本研究中的家庭是指以婚姻、血缘、收养或感情等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以同住一起、经济共有、共同分享情感为主要特征的初级社会生活单位。而罕见病儿童家庭则是指与至少一位罕见病儿童患者长期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组织。关于儿童的定义,本研究依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界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罕见病儿童指18岁以下患罕见病的儿童。
三 家庭抗逆力
抗逆力是个人在因应重大危机时所显示的能力。抗逆力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性、个人所拥有的动机性力量或者一个过程。该过程描述了个人如何使用和发展他/她自身和外在的资源来处理生活困难以及完成个人成长。此概念在国外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陈蓓丽,2013: 17)。
当对家庭抗逆力进行定义时,正如定义个体抗逆力一样,关注点主要是家庭在面对压力时展现的优势而非病理上。这种非病理性的定义可以帮助家庭寻求精神健康服务,而不必担心被评判或责备。Walsh把家庭抗逆力定义为从逆境中恢复,并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善于应变的能力(Walsh, 1998)。他于2002年扩展了这一定义,认为家庭抗逆力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面临困境或危机时,在信念体系、组织模式及沟通过程等方面应对危机与逆境的能力,以及透过危机达成个人和关系改善的能力(Walsh, 2002)。这个定义包括了更多元素:面对压力事件,不仅能够应付和幸存而且还能够用逆境去促进个人能力的提升和关系的改善。这个定义认识到了在逆境之中,个人能力增进和关系提升的潜能。McCubbin等于1996年将家庭抗逆力定义为家庭利用其行为模式、技能去谈判、应对乃至在困境和危机中茁壮成长的能力(McCubbin et al., 1996)。Hawley等于1996年将家庭抗逆力定义为一种路径,只要遵循此路径,无论在当前还是以后,家庭只要在面对压力时都能够适应并健康成长。他们相信具有抗逆力的家庭面对压力状况能够用独特的方式积极应对。这种应对能力依赖于以下几个因素:家庭发展水平、风险和保护性因素以及家庭共同的信念(Hawley et al., 1996)。几年之后,Patterson于2002年也定义了家庭抗逆力,家庭抗逆力是一个适应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重大的逆境或压力面前,家庭利用这一过程去适应并发挥家庭的功能(Patterson, 2002)。虽然这些定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每一个定义都有其不同的强调点。Lee等把抗逆力定义为当家庭面临内部或外部压力时,能够根据家庭信念或价值观系统而产生家庭功能变化的一个特征(先天或后天)(Lee et al., 2004)。有研究基于慢性疼痛模型提出家庭抗逆力的概念,认为家庭抗逆力是一种有利于家庭改变和增长的潜能,透过这一潜能,在面对突发或长期的困境或挑战时,家庭变得更富有资源。该研究通过慢性疼痛管理模式指出,整体大于部分,个人的抗逆力不能保证家庭的抗逆力,家庭中的成员和在社区一样,是有共同的抗逆力的,而不仅仅是按照相似的方式生活(West el al., 2011)。
家庭抗逆力研究的代表人物McCubbin夫妇发现家庭抗逆力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应包括家庭的形态或对危机的回应。他认为家庭抗逆力的构成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第一,家庭保护因素,指家庭成员处理发展阶段的转变以及努力提升家庭和谐与平衡的能力;第二,家庭恢复因素(McCubbin H. I. &McCubbin M. A., 1996)。有关儿童长期照护的研究显示,家庭整合、家庭支持和自尊建立、家庭的娱乐取向、控制和组织、家庭的乐观与优势等家庭恢复因子对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有直接关系。家庭抗逆力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Walsh则从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家庭沟通与问题解决历程三个系统来分析家庭抗逆力展示过程。他认为家庭信念系统涵盖价值观、态度、偏见与假设等,主要可分为三项范畴:对逆境意义的诠释、克服逆境的正向前瞻、超越性与精神性(Walsh, 2006)。这些信念会融合成一套家庭的基本假定,影响情绪反应,促成决定,最终引发行动。信念系统是影响家庭功能运作的重要因素,也是培养家庭抗逆力的重要力量。如果视家庭为一个运作单位,那么当面对困境时,家庭系统及文化中最主要的信念,是影响家庭最大的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成员间仍会有相异的观点、生活方式与认知,这与成员特质、时间因素或关键事件等,都可能对家庭信念系统产生影响。家庭组织模式对家庭抗逆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动员家族、组织资源、处理压力、调整组织结构,这是有效处理危机,并因应长期逆境的方法。家庭组织模式因外部与内部的各种规范维持及文化与家庭信念系统、家庭成员对彼此的期待等因素影响而呈现不同的组织模型,并影响到家庭与成员的整合与适应。
综观有关文献,笔者对目前家庭抗逆力的研究框架做以下整理(见表1-2)。
表1-2 家庭抗逆力研究框架梳理

由表1-2可以看出,家庭抗逆力既可以看作单个的家庭成员的抗逆力(Cowan et al., 1996; Hetherington&Belchman, 2014; Kim, 1998; Woodgate, 1999),也可以看作以家庭为单元的抗逆力(Antonovsky, 1979, 1987; McCubbin H. I. & McCubbin M. A., 1988; Patterson, 1995; Walsh, 1996)。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家庭抗逆力,灵活性、抗压性、正向思考、应对(问题解决)、控制感(平衡性)、适应(适应能力)、社会融合和富有智慧都是家庭抗逆力的共同特点。区别在于,从个体角度来看抗逆力,强调成熟性、赋权、创造性和归属感。培养个体抗逆力的因素包括灵活性、对社会支持的运用、回弹、高期望、幽默、自我效能感和自尊等。而从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家庭抗逆力更强调家庭凝聚力、义务、交流、家庭优势、联结性、意义性、灵性和反弹性。
综合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对家庭抗逆力研究的视角不同,对其定义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单从家庭作为整体来定义的家庭抗逆力又可以分为三种(冯跃,2014: 141):第一,作为一种适应方式的家庭抗逆力,指家庭成员面对压力时的适应及转变过程,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积极面对危机境遇,整合各种风险及保护因素,彼此间达成共识性愿景并生成发展性路径(Hawley et al., 1996: 283-298);第二,作为一种保护性因素的家庭抗逆力,McCubbin夫妇及其同事在多年的家庭抗逆力模型研究的基础上,从自我修复的角度,指出家庭抗逆力是个体和家庭成员在面对压力和逆境时所表现出的积极的行为模式和应对策略,以帮助作为功能性实体的家庭尽快从危机中恢复出来,确保家庭成员的幸福安康(McCubbin et al., 1996:23);第三,作为一种关系构建中的家庭抗逆力。在Walsh看来,作为独立功能单位的家庭,在面对重大逆境或破坏性的生存挑战时,常常要通过不同的应对方式加以调适。因此,家庭抗逆力指的是家庭在面对种种不利环境时获得的机智灵活的反弹能力,以及从中体现出的积极的危机承受能力、挑战能力以及自我修复能力等(Walsh,2006: 7),家庭抗逆力不只是压力管理或经受逆境考验,还包含了个体及社会关系层面的潜能转变与提升的含义。上述定义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及角度,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勾勒出家庭抗逆力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性实体单位所具有的建构性意义。但无论何种视角,有关家庭抗逆力的定义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第一,均包括了家庭在呈现脆弱性(指造成家庭失功能的危险因素,如生理、经济)或家庭出现危机(指持续使家庭处于不稳定、混乱、失能)时,能发挥正向作用的一面;第二,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家庭抗逆力展现历程概括为两阶段三系统。两阶段指适应(包含保护因素)和调适(包含回复因素)两个阶段。发挥关键作用的三个系统是: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家庭沟通与问题解决历程。
基于先行研究成果,特别是借鉴家庭抗逆力研究代表人物McCubbin夫妇和Walsh对家庭抗逆力两阶段和三系统的观点,本研究将家庭抗逆力定义为罕见病儿童家庭在面临罕见病这一困境或危机时,作为一个整体运用各种资源及其行为模式,应对乃至在困境和危机中茁壮成长的能力。从更具体的操作化定义来说,本研究以罕见病儿童家庭特征为基础,综合学者对家庭抗逆力的定义和临床工作中家庭抗逆力的评估与介入的指导原则,将家庭抗逆力展示过程分为三个主要系统来阐释:家庭图式系统、家庭组织系统及家庭行为系统,在研究中探索中国文化语境下罕见病儿童家庭在三大系统内具体包含的因素和展现过程。这三个系统是本研究中辨识家庭优势与弱点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个架构作为一份地图,帮助笔者在进行家庭访谈时,把焦点集中在关键过程上,指引笔者关注家庭功能中的重要元素,在研究的过程中得以突出或强化家庭抗逆力(Walsh, 2003a: 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