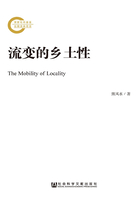
一 植根于“土”上的生活
南村村民的生存和生活资料来源于土地上种植的各种农作物,村民靠土地来吃饭。人多地少的压力使得村民在土地上精耕细作,把土地使用到极致,农民利用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时令季节来合理安排各种农作物的种植,说得更直白些,就是安排好时间,使土地在一年四季都能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不让土地荒着。村民从事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只要庄稼地里能够种植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去市场上买,而是想尽办法在土地上种植,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获得收入的机会,没有收入就只能尽量压缩支出,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就显得特别多。主粮如水稻、红薯等,其他农作物,如油菜、花生、小麦、芝麻、棉花、大豆、玉米等,再有就是在地里种植各种蔬菜,如白菜、萝卜、扁豆、黄瓜、茄子等,用以满足一家人全年的吃菜需要。实际上还有一些作物笔者无法用普通话的书面语言表达出来。这种需要什么就在土地上种植什么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方式,决定了村民很少在市场上进行过多的交换,一方面,需要什么就种植什么,大部分的基本需求可以满足,不需要去买;另一方面,需要什么就种植什么使得种植农作物的品种很多,这样每一种作物的产量就很低,很少有拿到市场上去卖的。村民从商店里买东西回来,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春节时准备年货,有些物品需要到街上去购买;或者家里来了重要客人,会到屠户店里买些猪肉回来,用以招待客人。二是购买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如必要的化肥和农药等。除了这两种情况外,村民很少从市场上购买东西用以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都是通过在“土”上种植作物来满足需求。由于人多地少的先天不足,即使精耕细作,把土地利用到最大化,村民的目标仍然是把肚子填饱,人们生活在生存的边缘,南村经济属于“生存型经济”。以上描述的南村村民生活实际上是1980年以后的情况,1980年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的积极性得以发挥,才基本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在这之前的南村,生产合作社的劳动方式无法调动村民积极性,偷懒现象普遍存在,效率低下,村民实际上是处在半饥饿状况,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饿死了很多人,生活极其贫穷,处于饥饿型状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直到村民大规模外出打工前,村民的生活就处在这种基本上能吃饱(稻谷加红薯)的生存型状态。
村民的基本需要都是从土地上得到满足的,土地成为村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村民世代在土地上劳作,很忠诚地向土地讨生活,他们离不开土地,土地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生产和生活的命脉:‘万物土中生,离土活不成。田地是活宝,人人少不了。田地是黄金,有了才松心。’因此可以说,‘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只有有了土地再加上辛勤的劳动才可获得生活的来源。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使中国的重农思想不断加强。” 土地的重要性不仅使农民形成了浓厚的重本轻末的土地依赖意识,还造成了他们安土重迁的行为特征。农民不愿轻易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居住地,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家人、亲戚、邻里和朋友,有他们熟悉的一草一木,更重要的是有他们生存的依托——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拥有土地就拥有了未来生活的希望,而一旦失去土地便要委身于人,失去生活的自主,中国历来的农民起义都是为取得土地揭竿而起,对土地的渴望可以让农民付出生命的代价。土地凝结着农民最为朴实的情感,在农业社会里延续着人类生存的本能,提供着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的理想是“两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对农民来说,有了土地,才有了根和灵魂,对于以农为生、以乡为居的农民来说,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充满着深厚的爱恋深情,如果没有异常的变故是很难使他们与乡土相分离的。“穷家难舍,乡土难离”“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农民对于“土”和“乡”有着一种深厚的朴素情感。
土地的重要性不仅使农民形成了浓厚的重本轻末的土地依赖意识,还造成了他们安土重迁的行为特征。农民不愿轻易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居住地,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家人、亲戚、邻里和朋友,有他们熟悉的一草一木,更重要的是有他们生存的依托——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拥有土地就拥有了未来生活的希望,而一旦失去土地便要委身于人,失去生活的自主,中国历来的农民起义都是为取得土地揭竿而起,对土地的渴望可以让农民付出生命的代价。土地凝结着农民最为朴实的情感,在农业社会里延续着人类生存的本能,提供着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的理想是“两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对农民来说,有了土地,才有了根和灵魂,对于以农为生、以乡为居的农民来说,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充满着深厚的爱恋深情,如果没有异常的变故是很难使他们与乡土相分离的。“穷家难舍,乡土难离”“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农民对于“土”和“乡”有着一种深厚的朴素情感。
农村有句古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话在南村也是适用的。南村的自然条件除了田地之外,就是村庄周围有众多的河流,渔业自然成为村民最主要的副业。也正是因为这些河流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减轻了饥荒的程度。有很大比例的村民家庭拥有小渔船,有一些渔网和虾笼之类的工具,可以捕鱼虾,鱼虾主要用于自家食用,村民的饭桌上一道最主要、最常见的菜就是鱼虾。但是,鱼虾是不能代替稻谷和红薯的,鱼虾只能用来做菜,不能当饭吃,鱼虾只能减轻饥荒的程度,不能彻底解决饥荒的问题。村民捕捉的鱼虾中也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拿去卖,但由于整体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鱼虾的价格非常低,拿去卖钱不是村民捕捉鱼虾的主要目的。碰上梅雨季节,捕捉回来的鱼虾因为无法晒干,很快就腐烂变臭。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经常把鱼虾煮熟,当作猪食给猪吃。河流除了可以给村民提供鱼虾之外,还可以提供其他的一些东西,如河里的水草,村民经常把河里的水草拉上来,切碎煮熟后作为猪食,用于喂猪。还有河里的沙子,村民把沙子从河里挑上来,用一张网过滤以后,可以得到较好的细沙,细沙可以用来和成泥浆盖房子。当然,有利就有弊,河流众多使得村民最怕的就是闹洪灾,1953年、1998年、1999年等几次大洪灾,就让村民损失惨重,庄稼甚至房屋被淹,有些村民无家可归。
除了渔业以外,村民还有其他的一些副业,主要是用于满足村庄和村庄周边的村民日常生活需要,如裁缝、石匠、木匠、篾匠等,这些职业的工价都很低廉,一年下来赚不到几个钱。副业都是村民的兼职,村民的主职是务农,在村民眼中,不务农就是不务正业。
自然经济条件状态下的南村村民,依附在土地上,自给自足、自耕自食、自织自穿,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村民不违农时,春耕秋收,年复一年地生产、消费,缓慢的生产节奏,养成了他们松懈而稳定的生活方式。村民坚持自发形成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不离乡土,安身立命,生活在狭小而稳定的村落中,彼此都是熟悉的乡里乡亲,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原生态的乡土性正是孕育于凝固的“土”和封闭的“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