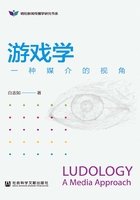
第二节 游戏的本质
游戏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不断被讨论的话题。前面的论述能够帮助我们形成对于游戏的基本认知。关于游戏本质的探讨,目前存在多种观点。陈连山在《游戏》一书中,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卷”“教育卷”,以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辞海》等中的相关概念出发,认为:“发现游戏的庐山真面目还要仰赖于游戏学的建立,即:把游戏作为一个主体,承认游戏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活动方式。”[48]作者在探讨游戏产生的根源的时候,认为:“动物的运动本能是游戏产生的基础”;“游戏行为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也存在于动物世界”,并举小狮子打闹产生满足、快感与美感的例子。“不过,我们通过动物的行为来判断其情绪,平和而玩耍,我们认为它们快乐;沉默而发怒,我们认为它们不快乐。这里的动物,应该是哺乳动物,因为其他动物,我们难以从外表判断。”作者得出结论:“游戏的本质是先于人类、更是先于人类文化而存在的。”[49]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游戏和娱乐之间的区别在于:首先,游戏的快乐与物质享受式的娱乐无关;其次,游戏所带来的快乐是一种人人共享的快乐……而商业性的娱乐活动往往是消费者单方面的娱乐;再次,游戏与其他娱乐之间的差异还在于参加者是否有自由参加和自由退出的权利。因此,游戏的本质“是使人获得纯粹的、与物质享受无关的快乐”。[50]笔者认为,一方面,游戏并不排斥物质手段。物质,对于游戏而言,是既不充分又不必要的条件。有物质,可以游戏;没有物质,也可以游戏。所以笔者认为真正的游戏不因为物质而受到牵绊。“乘物以游心”。何乐而不为呢?游戏以游戏自身为目的,这是游戏的本质。在现实生活中,游戏能够超越物质,而非避开物质,才是最高境界。另一方面,游戏具有层次性和阶段性。现实生活中,不能非常严格地区分真正的游戏。它具有核心层,这是游戏存在的基础;也具有外在层,这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游戏是否纯粹,不应该成为衡量游戏是否存在的标准。不纯粹的游戏,只要具备游戏精神,也可以视为游戏。而这才是生活中的游戏的常态。
在游戏的具体过程中,可能某一个阶段是不符合游戏所要求的纯粹的,例如会有嫉妒、仇恨、私利、投机取巧等功利行为,会有物质奖励的干预等,但是如果因为存在这些因素就否定这个游戏,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游戏的局部“变化”不影响整体上的游戏精神,相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游戏过程中,人出现违背游戏精神的缺陷,然后开始得到纠正(自我纠正或者游戏调控),最终以真正的游戏精神结束游戏——这种情况往往成为游戏教育和游戏治疗所青睐的理想结局。因此,游戏有层次、有境界;境界有大小,但适合游戏的人即可;游戏的最高境界是游戏超越物质。有物,则“乘物游心”;无物,则“心游八极 ”。因此,游戏的本质是获得纯粹的快乐,但获得快乐的手段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游戏的本质和游戏的虚拟性、自由性、自足性、规则性、竞争性和运动性等元素,共同构成了游戏与其他概念的分水岭。
进而,游戏是否具有阶级性?游戏具有阶级性,这并非游戏本身的特征,而是人类历史附着在游戏身上的烙印。比如,竞技活动逐渐摆脱功利的压力,而逐渐成为一种快乐的手段,就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了贫富分化,也瓦解了原始公社竞技运动制度。部落贵族开始享有特权:良好的竞技器材、充裕的时间、专业的竞技机构等。而贫穷的子弟只有在家里接受劳动技能训练,或者在‘男丁营’中接受军事训练时有限地接触竞技运动”;“由于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文明时代的竞技运动不再把解决生存问题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开始具有新的独立的价值取向。娱乐性在竞技运动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51] 所以游戏的社会化是在某一阶层中被优先表达的,并且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繁荣程度与经济水平,即游戏自身也在不断分化,至少在形态上表现出不同群体的差异,因此游戏并非中立。
此外,游戏的阶级性也从游戏的政治功能方面表现出来。例如,印度板球是个极好的证明。“殖民当局推崇板球,把它看作是训练东方人道德的一种方式。支持板球的通常都是印度贵族里不甚重要的成员,因为板球比其他王室活动形式要廉价一些。作为印度小贵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的附属物,板球有三种吸引力:(a)在贵族休闲文化中它是一种男人的艺术,尤其在北方;(b)它的维多利亚证明书(比如拉吉);(c)作为其他王室公众景观有用的延伸,这些景观一直是印度王室责任和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52]印度王公们对板球的贡献在于:提供资金和空间支持;提拔出身卑微的优秀球手;从英国进口教练和器械,邀请英国球队,组织比赛和奖项等。可以说,板球成为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工具,而这种工具正维持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板球的印度化的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它是在印度的英国绅士、印度王公、流动的印度人(通常是公务员或是军人)之间复杂的、等级交错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最重要的是,事实上白人职业板球手(主要来自英国、澳大利亚)训练了本世纪最初十年出色的印度球员。”[53]其实,游戏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阶级流动的通道,因为“印度王公们支持板球,为的是进入维多利亚贵族世界,他们强烈反对民族独立运动,事实上为普通印度人掌握板球打好了基础,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板球上显示出来的卓越能力就成了印度人自己的骄傲了”[54]。这种阶级性使游戏参与了社会更迭与变迁的进程,也意味着游戏不仅具有单一的具体功能,而且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关联,并且互相作用,因此游戏最终的社会本质是作为一种媒介而存在,这种媒介在社会成员与社会、社会的不同层面等之间建立了复杂联系。
[1]崔乐泉:《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崔乐泉:《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3] 在胡伊青加的《人:游戏者》(2007年第2版)中,译者成穷在序言中回顾游戏理论时认为,柏拉图的《法律篇》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虽然涉及游戏思想,但着墨不多,因此西方思想对游戏的系统反思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乃至近代特别是到了康德那里,游戏现象才开始进入理论思维的视野。具体参见〔荷〕J.胡伊青加《人:游戏者》,成穷 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版,中译者序。
[4] 〔荷〕J.胡伊青加:《人:游戏者》,成穷 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7页。
[5]〔荷〕J.胡伊青加:《人:游戏者》,成穷 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2页。
[6]www.baidu.bake.com。
[7]http://www.chinabaike.com。
[8]崔乐泉:《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9]崔乐泉:《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0]蒋松卿:《围棋起源于何时》,《岭南文史》1995年第4期,第64页。
[11]柳慧玲:《论高尔夫球的起源与发展》,《第二届海峡两岸体育运动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第691页。
[12]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竞技运动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
[13]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竞技运动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14]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竞技运动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15]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竞技运动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16]崔乐泉:《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7]卢锋:《娱乐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8]卢锋:《娱乐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9]卢锋:《娱乐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0]崔乐泉:《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1]卢锋:《娱乐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2]卢锋:《娱乐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3]卢锋:《娱乐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4]卢锋:《娱乐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5]〔英〕克里斯·布尔,杰恩·胡思,迈克·韦德:《休闲研究引论》,田里、董建新 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26]卢锋:《娱乐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27]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电子游戏和儿童尤其是青少年成长之间的关系成为争议的焦点;因为游戏在传统社会中担负着重要的教育功能,但是电子游戏(尤其是网游等)一度“放大”了其负面影响。
[28]卢锋:《娱乐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29]卢锋:《娱乐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30]卢锋:《娱乐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31]卢锋:《娱乐体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32]〔英〕克里斯·布尔,杰恩·胡思,迈克·韦德:《休闲研究引论》,田里、董建新 等 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33]崔乐泉:《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引言。
[34]崔乐泉:《忘忧清乐——古代游艺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5]〔美〕阿瑟·阿萨·伯杰:《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36]〔美〕阿瑟·阿萨·伯杰:《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37]〔美〕阿瑟·阿萨·伯杰:《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38]www.youdao.baike.com。
[39]〔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郭发勇、周辉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原文则来自米哈伊尔·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论中的问题》,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4),巴赫金也是西方游戏史研究的代表者之一。
[40]〔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郭发勇、周辉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41]陈连山:《游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11-14页。
[42]Aaron Smuts,Video Games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 Newsletter,2005.
[43] Huizinga,John,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Boston:Beacon Press,1950.
[44] Callois,Roger,Man,Play,and Games.Trans.Meyer Barash,Chicago:Univevso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45] 张新军:《叙事学与电子游戏》,《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46]吴玲玲:《从文学理论到游戏学、艺术哲学——欧美国家电子游戏审美研究历程综述》,《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47]宗争:《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8]陈连山:《游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49]陈连山:《游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50]陈连山:《游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51]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竞技运动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52]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
[53]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
[54]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