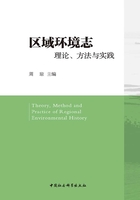
二 历史叙事的多种可能
口头的叙事,或者说以口头言说存在的知识包括历史知识也有其自身的价值。如也表达了一些不同于史官的另类的看法,无论这种史官的看法是否代表权力掌握者的观点。这就是现在人们较多地肯定口述史发出了底层人们的声音的原因。尽管口述史并非就只是底层的声音。无论是底层的声音或者边缘群体的声音,抑或是也包含了一些并非底层的声音,但口述史都是这原有的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之声之外的声音。哪怕存在着不真实的问题,口述史也会迫使人们去怀疑原有的单一的历史叙事的权威性,至少也会促使历史叙事要更加警惕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
即使在不是直接讨论口述史的有关历史的思考中,已经书写成型的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是会受到不断的挑战的。阿多诺就认为在生存本能以及理性对自然的控制的推动下,“欧洲正史下掩藏着一部秘史”。[17]这部秘史“包含着被文明压制和扭曲了的人类的本能与激情”[18]。本能与激情被压抑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对自然的异化很可能进一步导致人自身的异化。从这个意义而言,口述史具有了协助人们宣泄本能与激情,调和人与自然关系进而调和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作用。以口头陈述为基础的口述史的叙事和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书写都同样是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观念的反映。这些反映都可能存在缺陷,只不过,口述史的问世使得历史这种观念的反映的缺陷更易于被人们所承认。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原有的社会结构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当今的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的进步等都使得人群流动的幅度、频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传统的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记录与书写方式难以满足人们对历史的多样性的理解以及对知识的多样性的求索。口述史有力地补充了传统史籍中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有所缺失的遗憾。更为重要的是补充了普通民众由于其身处的地位的不同而具有的对历史事实的不同的理解。事实上,人们在现实中记录历史知识的方法路径本身就是多样化的——精英和经典的思想是一类,生活世界中的“日用而不知的”常识是一类,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也是一类。因此,不仅仅经典著作因承载着历史信息而成其为历史文献,家训、族规、蒙学读物也可以成为历史文献,甚至报摊上的通俗读物、人们的热点公共话题也都可以为人类思想发展史做出特定贡献。[19]如《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时期开封市民多场景、多主题、多面向的日常生活,这对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的整体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是所谓正史所不能赋予的。与此相仿,口述史的方法使普通民众能够自己亲口讲出对自我的生活、民族、文化、社会及国家的历史的认识与理解。不同言说者的不同声音,是对之前保持沉默的一种打破。不同的声音好似不同的声部,“言为心声”式反映历史事实的口述史在实质上是一曲多声部音乐的创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人们可以看到整合不同的人对生活、对历史的不同理解从而形成历史发展的共同认识是非常必要的,但理想化的整合并非是同一乃至规训,而是允许不同的人去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形成复调的历史理解,使不同的认识可以因为对话的存在而最终消解其中的抵牾,使之共同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活水之源。
当世界诸多国家开始进行口述史的实践并开始有关口述史理论分析的时候,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时间的‘实地调查’”;[20]这些调查成果也包含了大量的口述材料,而且口述者或多或少能够现身。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学中“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思潮引导下的向外寻求方法也促进了口述史的实践和理论探讨。[21]在这里,可以看到国内口述研究的学术建构源头。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口述史工作实践与70年代作为学科概念得以引介进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口述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口述史”这一概念得以引入前,中国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进行了先行的口述工作探索。这愈加表明了人类心智中普遍同一性的存在及其在言说活动中的共同表现。人们在言说活动中意识到打破沉默、发出声音的重要性。
无论如何,过去那些被历史学家“疏远”的“在时间上与自己生活时代距离靠近的‘近历史’”[22]开始逐渐引起了学界内外的重视。人们对口述史的渴求甚至掀起了一场“当代中国的口述史运动”,而这场运动“缘起于破除政治迷信的思想解放大潮之中,当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造成了反思历史的强烈苛求,但传统学术体制的知识供给机能严重不足”。[23]这就不仅可以看到口述史具有对于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历史书写具有共同探索多声部的复调历史之探索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具有比所谓正史的更早地表达对世界的理解的意义。
作为历史叙事的另一种方式的口述史存在的意义还在于可以促使多种历史叙事的产生,并且为更多面向地理解世界产生动力。世界并不能理解为各种事物简单相加的总和,而必须被理解为任何事物可能存在的条件。[24]机械地将对不同事物的理解叠加后即认为获得了对世界的理解的做法,由于实践的创造性价值而不断调整为,通过讨论各种事物,从而理解事物得以存在的条件,即对现实世界以及观念世界的理解、把握以及调和。这就意味着,口述史的意义并不简单地在于在正史之外加上了另外一种历史。口述史通过激发不同声音的发出、不同声部的合作,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穷尽了对世界的理解,而是可能会使对世界的理解变得更为成熟和精深。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意欲对所有变化做横截面式的判定显然是不现实的,如何理解不断变化的世界恰恰需要汇聚各种个体、各种族群、各种文化的生活经历与生存智慧。这恰是口述史能够在实现这一目标中做出的应有的贡献。
各具独立旋律的叙事与书写理应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而形成复调历史。这种复调历史并非杜赞奇基于话语的争夺、控制、实施和操纵等角度去理解社会和历史的过程这种话语分析方法并以解构民族国家单线叙事为目的的复线历史。[25]葛兆光对杜赞奇基于复线历史观得出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之结论提出质疑,指出“‘中国’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原本就是历史的延续体,这与西方不同,中国并不是后设概念,因此,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是更为合适的研究进路。[26]依然基于文献而展开的历史,由于话语分析的使用,可以去挑战终极目的,是为民族国家站台的历史,但同时,这样的历史也同样需要去面对到底应该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还是应该从历史去拯救民族国家的挑战。
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书写本来也是一种历史事实的观念的反映。但是,由于缺少其他的以不同的方式产生的声音,这种观念的存在的东西更容易被当成了事实的存在,从而遮蔽了其心声的实质。正是在社会不断发展,无论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观念的更新还是技术方面的进步都已经为不同声音的发出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之后,其他的心声也有了表达的需要及条件。并且,这样的表达可以使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乃至观念存在的事实被确证。口述史存在的理由开始变得充分。哪怕口述史中存在的不够公正,不够全面,不够真实等的问题被指出,尽管毫无疑义这些问题应该被克服,但都不会使口述史丧失生命力。因为,口述史就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而且在承认自己是心声的时候可以再次明确文献历史也只是一种观念的存在。
或许,文献历史更加容易获得更多的观念与事实相符性的实证。关于历史的无规则的声音就是指对那些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未经整理的记忆的呈现。相对而言,文献记录的材料更能够便利地形成有规律性的书写的历史。口头言说因易变——造成易变的原因很多,如情景等影响——要在易变性的材料中建立逻辑关系就更加困难。但是,即使在比较中显示了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更具真实性,但也使人们更易发现这种历史也面临着对文献材料本身的采用是否有所取舍,取舍是否得当,书写是否秉笔直书等问题。对历史进行言说的言说者的身份多样性以及言说本身的多样性都表达了对多声部历史的诉求。无论是口述史还是文献历史,都是观念的存在,都需要进一步地自证其与历史事实的相符性。口述史的出现使得历史事实的言说获得了更多的可能,结果就是促使多声部的复调历史之形成不断成为可能,这是极具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