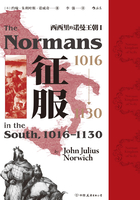
2 抵达
人口增长如此之迅速,以至于森林和土地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这些人离开了,他们放弃了贫瘠的土地,去寻找富饶的土地。他们也不满足于去服务他人,因为他们来到这里的人数如此之多。但是,像先前的骑士一样,他们认为所有的人应该臣服于他们,并承认他们为领主。因此,他们拿起了武器,破坏了和平的约定,完成了伟大的战争和侠义的功业。
——阿马图斯,第1卷第1章第2页
去伦巴第的首领们似乎既没有从需要他们帮助的战士那里得到任何引荐,也没有拿到任何条款,只是得到了鼓励而已。他们受到邀请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诺曼底的城镇和庄园,南方能够提供的充满愉悦的故事、现有居民的衰弱程度、等待诺曼人来取的奖赏,这些信息无疑传遍了各地。这样的故事对于任何人口中不可信任的那部分人来说都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最早进入意大利的诺曼移民尽管在表面上很像阿马图斯笔下的古代骑士,但是他们与他吟唱的加洛林传奇中的骑士并无一致之处,就毫不奇怪了。他们主要由骑士的幼子、乡绅的幼子所组成,他们不继承遗产,与其先前的家族并无密切关系。但是还有一群名声不好、想要挣得不义之财的专业打手和冒险家。很快还有一些一般的小混混也加入他们,他们一路穿过勃艮第(Burgundy)和普罗旺斯(Provence),人数不断增加。1017年夏,他们跨过了标志着教皇国南部边界的加里利亚诺河(Garigliano),直接前往卡普阿。按照先前的安排,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焦急等待的梅卢斯,此刻他正率领一群人准备立刻发动战斗。
伦巴第人的最佳战机,明显就是趁拜占庭一方还未弄清形势并寻求增援之前先发动进攻。因此,梅卢斯告诉他的新盟友,现在不能浪费时间,他立刻率领他们穿过卡普阿边界。结果他们出其不意地彻底打败了敌人。到了冬天,也就是第一年战争的末期,他们已经取得了几场有重要影响的胜利,甚至可以拿希腊人的弱小来开开他们最喜欢的玩笑。1018年9月,他们已经将拜占庭人从北部的福尔托雷河(Fortore)到南部的特兰尼之间的地区驱赶走了。但是在10月,形势突然逆转了。
在奥凡托河(Ofanto)的右岸,大概距离亚得里亚海4英里处,一块巨大岩石的影子依旧落在坎尼(Cannae)的土地上。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这里率领迦太基人对罗马人发动了罗马历史上最血腥和最具灾难性的打击。1234个年头之后,也是在这里,梅卢斯率领的伦巴第和诺曼军队对阵拜占庭军队。拜占庭一方的领导者是卡塔潘之中最伟大的一位——瓦西里·沃约阿尼斯(Basil Boioannes),在他的领导下,梅卢斯一方遭受了更具灾难性的打击。从一开始,拜占庭一方在人数上就更多一些,而且在沃约阿尼斯的要求下,皇帝瓦西里二世(Basil Ⅱ)从君士坦丁堡派去了重兵。阿马图斯写道,希腊人像倾巢而出的蜜蜂一样遍布在战场上,他们的长枪又直又密,宛如插满藤条的田地。还有另一个对梅卢斯的失败具有推波助澜作用的因素:诺曼人的军事力量早就闻名于拜占庭的首都,因此瓦西里为他的军队也配备了来自北方的骑士——一支瓦兰吉卫队(Varangian Guard)的分队,这支部队是30年前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与瓦西里的妹妹结婚时送给他的维京军团。伦巴第人奋力战斗,却是枉然,大部分都遭到了屠杀,只有少数人得以幸免。这次失败之后,梅卢斯在普利亚让伦巴第人获得独立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梅卢斯本人设法逃脱,在各公爵领以及教皇国之间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几个月,最终在班堡(Bamberg)的西方帝国皇帝亨利二世那里获得了避难之处。两年之后,伤心绝望的他在班堡去世了。亨利作为拜占庭控制意大利南部的主要对手,总是竭尽全力帮助梅卢斯,并在自己新修的主教座堂里为梅卢斯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还为他修筑了一座宏伟的墓穴。不过,无论是石匠的高超技艺,还是他去世之前亨利所授予的普利亚公爵的头衔,都无法改变他失败的事实。更糟糕的是,他决意带给他人民的自由,由于他不经意地邀请了诺曼人而永远无法实现了。他已经让诺曼人尝到了血的滋味。
诺曼人在坎尼勇敢地作战,但是损失惨重。他们的首领吉尔贝(Gilbert)阵亡,军队也大量减少了,他们在战斗结束之后重新集结起来,并推举其弟雷努尔夫(Rainulf)为继任者。由于梅卢斯已经不在了,在找到新的恩主之前,他们必须自食其力。他们沮丧地跑到山里,去寻找一块可以巩固自己力量的地方,一块可以用作他们的永久大本营的地方,可以为不断从北方到来的新移民提供聚集点的地方。他们最初选择的地方不吉利。在修筑据点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比坎尼之战更加羞辱的失败。普利亚的威廉告诉我们,突然出现的大群青蛙困扰了他们,青蛙实在太多了,他们甚至无法继续工作。青蛙的呱呱声连绵不绝,他们狼狈地撤退了,找到了另一个更加适合的地点。不过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也不长。多亏了不断加入的新来者,他们的人数不久就大大超过了以前。此外,尽管他们第一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但是他们作为战士的声誉仍旧无人可比。各方力量都需要他们的效劳。
南意大利这口大锅永远无法从沸腾中冷却下来。当时,这块土地被四大势力所包围,土地上遍是频繁的争斗。这块土地上有四个族群、三个宗教,还有数量不断变化的一些独立、半独立或发动叛乱的国家和城市,它们之间的战斗分裂了这片土地。在这样的土地上,强大的臂膀和锋利的剑刃永远不会失业。许多年轻的诺曼人被吸引到萨莱诺的盖马尔那里。其他人则到了他的妻舅兼对手卡普阿亲王潘都尔夫(Pandulf)那里,他号称“阿布鲁齐之狼”(Wolf of the Abruzzi),其力量和野心引起了邻邦的强烈关注。还有一些人倾心于那不勒斯、阿马尔菲和加埃塔。与此同时,卡塔潘沃约阿尼斯正在修筑新的据点,意图巩固普利亚的防线,巩固其胜利,修筑据点的地方是位于亚平宁山脉通往外部平原道路上的特罗亚(Troia)。由于缺乏可用于建造永久要塞的力量(瓦兰吉卫队在获胜之后已经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只得去别处寻找人手。卡塔潘一眼就能认出优秀的战士,而诺曼人毕竟只是雇佣兵,因此毫不奇怪,在坎尼之战结束一年多以后,装备精良的诺曼战士策马进入普利亚,为拜占庭守卫法律上的领土,对抗邪恶残忍的、制造麻烦的伦巴第人。
这样转变效忠对象、轻易重整军队的气氛,或许对诺曼人的利益而言是一种伤害。确实有人可能会想,他们的目的是不是要增强自身的力量,以实现最终统治半岛的目标呢?诺曼人本应该保持团结,而不是无目标地分散在寻求他们帮助的无数势力之间。但是在早期,建立统治的想法还没有形成,诺曼人也没有那么团结。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身利益,而且就算他们确实权衡了所有问题,民族的抱负也只会居于可怜的第二位。诺曼人的好运就在于,这二者经常结合在一起。而且矛盾的是,正是他们明显的不团结,才为他们最终的征服扫清了障碍。如果他们一直是团结的,他们就不会搅乱南意大利的力量平衡。他们的人数偏少,所以无法独自占据优势。他们派别众多,无法联合起来同时支持某一个势力。通过分裂,他们不断改变自己的盟友和图谋,他们在参与的所有小型争斗中几乎都站在胜利者一方。而且,他们可以阻止任何单个势力变得过于强大。支持所有势力,等于没有支持任何势力;听命于最强的竞争者,也听命于每一个别的竞争者,他们这样便保持了行动的自由。
诺曼人并不是唯一在坎尼之战后必须思考自身地位的势力。坎尼之战后,拜占庭势力在整个普利亚得到了重建,拜占庭在整个意大利的声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以想见,这或许对各个伦巴第人的公爵领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早在1019年,卡普阿的潘都尔夫就真诚地与希腊人建立了联盟关系,他走得如此之远,甚至将首都的钥匙送给拜占庭皇帝瓦西里。在萨莱诺,盖马尔为了避免摆出扩张性的姿态,也一样毫无保留地表明了支持的态度。最令人惊讶的(至少乍看之下是如此)是卡西诺山的态度。这里的大修道院一直被认为是南意大利拉丁事业的拥护者,它代表的是教皇和西方帝国皇帝,因此它一直支持梅卢斯和他的伦巴第人,在坎尼之战以后同样为他的妹夫达图斯提供了庇护——达图斯在之前的1011年于伦巴第战败后,待在修道院的一座位于加里利亚诺河河岸上的武装塔楼里。仅仅数月之后,卡西诺山修道院也宣布支持君士坦丁堡。仅有贝内文托亲王仍旧效忠于西方帝国。
所有这一切对皇帝亨利而言都是坏消息,对教皇而言则更糟。虽然本笃八世为人正直,道德上也无瑕疵,①却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人物。作为图斯库鲁姆(Tusculum)的一个贵族家庭的成员,他在1012年当选为教皇的时候是否已经被授予圣职都是个问题。在担任教皇的12年时间里,他表现得更像是一个政治家和行动家,献身于让教皇与西部皇帝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意大利从所有其他势力手中解救出来的事业。因此他曾在1016年亲自率领一支军队对抗撒拉逊人。对抗希腊人时,他为梅卢斯和达图斯提供了所有自己能提供的援助。他两次与卡西诺山当局协调,为上述两人在加里利亚诺塔提供避难所。他此时看到自己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拜占庭的势力突然增长到他此前从未见过的程度。卡西诺山的背叛肯定是一次重击——虽然如果他记得以下两件事的话,会更容易理解一些:修道院院长阿特努尔夫(Atenulf)是卡普阿亲王潘都尔夫的兄弟,院长还在拜占庭治下普利亚附近的特兰尼神秘地获得了一大片地产。更为严重的是,希腊人的持续扩张带来了危险。获得了彻底胜利后,拜占庭人为什么要满足于领土仅限于卡匹塔纳塔呢?占用了瓦西里二世大量精力,为他赢得了“保加利亚人屠夫”(Bulgaroctonus)绰号的巴尔干战争如今已经结束,他认为教皇国这块肥肉已经是囊中之物了。一旦沃约阿尼斯渡过加里利亚诺河,便可长驱直入,直抵罗马城下。图斯库鲁姆伯爵们的长期敌人——险恶的克莱森提(Cresccntii)家族知道如何将这一灾难转变成他们的优势。上一次教皇前往阿尔卑斯山以北已经是一个半世纪之前了,但是本笃在得到卡西诺山的消息之后,没有再犹豫。1020年初,他动身前往班堡,去同他的老友兼盟友亨利二世商谈事态。
如果不认真想想教皇和皇帝分别坐在对方的位置上会不会更合适,是不可能了解本笃和亨利的。“圣人亨利”的绰号名副其实。虽然亨利的事迹可能不足以被封圣,他却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获得了这项荣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妻子卢森堡的坎尼贡德(Cunégonde of Luxemburg)的贞洁生活。虽然他的虔诚与迷信相随,但是他依然是一位拥有虔诚信仰的宗教人士,他在生活中最热衷的两件事就是修建教堂和宗教改革。这些精神上的事业并没有阻止他以惊人的效率来统治那庞大的帝国。尽管亨利一直干涉教会事务,但是从 1012年他还是德意志国王②的时候开始,他和本笃就是好友了,他支持本笃在教皇选举中对抗对手克莱森提乌斯(Crescentius)。他们之间的友谊,又因为本笃干预了亨利的皇帝选举,在1014年主持了亨利和坎尼贡德的加冕仪式而得到了加强。不仅如此,亨利的宗教观点和本笃的政治观点相一致,两者的友谊便进一步得到了巩固。直到此时,帝国和教皇国之间那长期而痛苦的争斗还未开始。斗争在不久后就会到来,而且将在两个多世纪以后腓特烈二世在位时达到高峰。此时二者相处正欢,对其中某一位的威胁也是对另一位的威胁。
1020年复活节之前,本笃抵达了班堡,在亨利新修的主教座堂里举行了盛大的节日庆典,然后与他开始商谈。起初,他们让梅卢斯讲述南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分析拜占庭的优势和劣势。但是在教皇抵达一周后,“普利亚公爵”突然去世了,只剩他们两人继续商谈。一直很敏锐的本笃认为,必须采取的行动显而易见:亨利必须率所有军队前往意大利。在某个恰当的时候,教皇也会加入这场行动,而行动的目的不是将拜占庭彻底驱逐出去——这是之后的事情——而是显示西方帝国和教皇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力量,它们准备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会给那些在联盟中摇摆不定的小城市、弱小的伦巴第贵族们注入新的信心。与此同时,这还会让沃约阿尼斯确信希腊人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都会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亨利虽然对此表示同情,但是没有立刻被说服。情况很微妙,希腊人还没有在事实上越过他们的边界。尽管亨利没有真正承认这些边界,但是最近拜占庭人行动毕竟是因为伦巴第人发动的叛乱,很难将拜占庭的行动定性为入侵。伦巴第人的公爵领和卡西诺山修道院的态度确实是令人焦虑的原因,但是就亨利所了解的,他们很看重自身的独立,不愿意成为拜占庭的附属。没有皇帝的支持,远征的队伍就不可能达到本笃所希望的规模。教皇在6月返回意大利之时,皇帝仍然没有最终表态。
亨利犹豫了一年,当年相安无事。随后在1021年6月,沃约阿尼斯开始了行动。通过之前与潘都尔夫的金钱交易,希腊人先遣军队进入卡普阿,所向披靡,直至加里利亚诺河畔达图斯居住的塔楼。达图斯将这座塔楼当成自己和一群伦巴第追随者和一批诺曼人的大本营,他们得到了教皇的庇护。即便在卡普阿及卡西诺山转向拜占庭后,他还是决定坚守在这里(达图斯从未显示出过人的智慧)。这座塔楼本来是用于抵挡撒拉逊入侵者的庇护所,用来防御撒拉逊人够用,却无法长期抵御装备精良的希腊人。达图斯和他的部下顽强地抵抗了两天,在第三天只好投降。诺曼人被释放了,但是伦巴第人遭到了屠杀。达图斯本人被铁链缚住带到巴里,他在巴里骑着毛驴游街。1021年6月15日夜晚,他与一只公鸡、一只猴子和一条蛇一起被缝进一个麻布袋,被扔进大海。
这桩暴行的消息迅速传到了罗马和班堡。达图斯曾经的私人朋友本笃在这次潘都尔夫和修道院院长阿特努尔夫的新阴谋中陷入丑闻,这两人因为一笔可观的奖赏而出卖自己同胞的事情广为人知,而这位同胞是最后一位有能力举起伦巴第独立大旗,公开承诺将希腊人驱逐出意大利的人。此外,正是教皇建议达图斯躲避在塔楼中,并与卡西诺山协商为其提供便利。教皇国的荣耀因此遭到了出卖,这是本笃永远不会原谅的罪行。他向班堡的亨利写信,他通过写信便能在回到意大利之后持续对亨利施压,现在他在信件中传达了更为紧迫的消息。达图斯的命运只是个开头。此次行动的胜利会鼓励希腊人采取更激进的行动。趁着还有时间,他们必须采取更强力的行动。亨利不再闪烁其词,1021年7月,他在奈梅亨(Nijmegen)的会议上做出决定,想尽快率军前往意大利。夏天剩下的时间和整个秋天,亨利都在做准备。12月,庞大的军队出发了。
此次远征的初衷是展示力量,事实也的确如此。此番进军时,军队被分为三个部分,指挥权分别归于亨利和他的两位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皮尔格里姆(Pilgrim)和阿奎莱亚大主教波波(Poppo)。第一支部队在皮尔格里姆的领导下按照命令从意大利西部进发,穿过教皇国,抵达卡西诺山和卡普阿,在那里以皇帝的名义抓捕阿特努尔夫和潘都尔夫。据说该部队由2万人组成,尽管这一数字值得怀疑。第二支部队估计由1.1万人组成,在波波的率领下穿越伦巴第和亚平宁山脉抵达普利亚边境,并在这里按照事先计划和亨利率领的主力——其军力远超过其他两支军队——集结,再沿东部的道路直抵亚得里亚海边。这支联军将深入内陆,围攻特罗亚,这里坐落着沃约阿尼斯修筑的、由诺曼人防守的新拜占庭堡垒,它被公认为堡垒的典范。
皮尔格里姆按照指示直奔卡西诺山而去,但是他抵达的时间太晚了。这里的修道院院长正确地估计到了本笃的愤怒,知道来者不善。得知帝国军队正在靠近,院长立即逃往奥特朗托,并迅速从那里登船,意图前往君士坦丁堡。但是报应还是降临在他头上。在他离开修道院之前,愤怒的圣本笃显现在他的面前,告诫他,他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上帝的不悦,还说他即将为自己的罪恶而付出代价。果然,他的船刚驶离港口,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出现了。1022年3月30日,阿特努尔夫乘坐的船沉没了,他和其他人一起溺水而死。与此同时,皮尔格里姆继续向卡普阿进发。潘都尔夫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组织居民去城墙上守备。但是他的臣民不再那么拥护他。大主教的军队攻来时,他发现臣民的忠诚已有所动摇。他的随从中有一些诺曼人,他们不喜欢这位前恩主,正确地判断了倒向哪边对自己有利,就暗中为帝国军队打开了城门。皮尔格里姆由此得以进入卡普阿,懊恼的王公只好投降。
按照最初计划,现在皮尔格里姆要向东与其余军队会合。但是在此之前,他决定前往萨莱诺,在那里的盖马尔虽然行为没有他妻舅那么恶劣,却仍然公开表示亲拜占庭,如果他受到的打击得以恢复的话,就有能力在将来制造麻烦。但是很快皮尔格里姆就发现萨莱诺和卡普阿的差别相当大。这里防御坚固,并且布防严密,因为盖马尔的受欢迎程度和潘都尔夫的被讨厌程度一样,他的诺曼守军并没有因大主教的军队而焦虑。该城被围困一个多月,尽管面临极大的压力,却明显没有投降的迹象。同时时间在流逝,在自己与皇帝之间,皮尔格里姆还有一段很艰难的翻越高山的道路要走。最后双方签署了一个停战协议,皮尔格里姆同意放弃围攻,以换取一部分人质。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了后方的安全后,他离开萨莱诺,向内陆进发。
亨利进军的速度也非常快。虽然军队有些笨拙,加之阿尔卑斯山严酷的冬天,他和旅途同样不顺畅的大主教波波还是按照原计划于1022年2月中旬会师。随后他们一起向内陆进军,抵达一个靠近贝内文托的地区,教皇在这里等待他们。3月3日,本笃和亨利一起以正式仪式进入贝内文托。他们在那里待了四周,进行休整,收取信件——也许是在期望能收到来自皮尔格里姆的消息。同时,军队也在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在该月月末,他们决定不再因为等待大主教皮尔格里姆而拖延,转而进军特罗亚。
沃约阿尼斯一如既往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帝国军队通过山的隘口,出现在普利亚平原上,对他们来说,特罗亚这根巨大的刺看起来是无法摧毁的。特罗亚城紧邻拜占庭领土和贝内文托公爵领的边界,城镇本身就是很明显的威胁。但是教皇的坚定决心与皇帝的虔诚信念做出了必要的表率,4月22日,围攻开始了。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局面没有什么进展,天气越来越热,胶着的情况只有在新的消息传来后才得以打破:皮尔格里姆正率军从坎帕尼亚(Campania)前来增援,潘都尔夫在皮尔格里姆的军中备受煎熬。阿特努尔夫的命运没有令亨利动容,据说,他只是念诵了《诗篇》第7篇中的一段③,随后便离开了。他当场判处潘都尔夫死刑,不过大主教为潘都尔夫求情,因为他在翻越群山的过程中对犯人心生喜爱。在劝说下,亨利为潘都尔夫减刑,将其关押在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一所监狱里——很久以来,很多人都希望这种仁慈的方式能让囚徒感到懊悔。“阿布鲁齐之狼”被人拴着铁链带走了,围攻仍在继续。
和同名的安纳托利亚城市④不同,特罗亚坚持到了最后。一位亲德意志的编年史家试图强调亨利最终趁着暴风雨占领了该城。一位以不可靠而臭名昭著的修士拉杜尔夫·格拉贝(Radulph Glaber)(他想象力之原始只有他的私生活可以比拟,他因为糟糕的私生活而被众多修道院驱逐,他被驱逐的次数比11世纪的任何文人都要多)讲了一个非常牵强附会的故事,在故事里,一位年长的隐修士拿着十字架带领城中的所有居民排成长长的队伍出降,亨利看到这场景时,心都融化了。但是,如果特罗亚真的投降了,相关事情居然没有出现在任何当时南意大利的记录中,这说不通。而且如果投降了的话,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沃约阿尼斯会在此后立即给予该城新的特权以作为忠诚的奖励。
因此,亨利没有获得胜利。他无法一直围攻下去。炎热的天气已经造成了损失,在普利亚肆虐到20世纪的疟疾在他的军队中流行起来。6月末,他决定放弃围城。毁坏了营地之后,饱受胆结石折磨的皇帝骑马带领庞大却士气消沉的军队向群山走去。这不是第一支被南意大利的夏天所征服的欧洲大军,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也不是最后一支。亨利在卡西诺山见到了更早到达的教皇,他们在这里待了一些时日,本笃自己忙于新任修道院院长的就职仪式,皇帝则希望有奇迹能消除他的结石(我们知道他成功了)。教皇和皇帝随后短暂地访问了卡普阿,接待者泰阿诺(Teano)伯爵也叫潘都尔夫,他入主了那位耻辱的同名者的王宫。随后教皇和皇帝便经由罗马前往帕维亚,去参加由教皇召集的有关宗教改革的重要会议。这样的集会对亨利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他在那里一直待到8月才返回德意志。
他的远征只能勉强算成功了。皮尔格里姆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潘都尔夫和阿特努尔夫均从舞台上消失。卡普阿和卡西诺山就很容易对付了,与此同时,来自萨莱诺和那不勒斯的人质(后者提供了人质,以免遭大主教军队的围攻)保证在沿海地区不会出现麻烦。另一方面,普利亚战役是一次惨败。特罗亚的坚定立场证明了帝国军队在意大利的无能——近6万军队竟无法降伏一个在4年前还不存在的小山城。更糟的是,军队由皇帝亲率,皇帝个人的声誉遭到了重创。计划、修筑、加固并迁来人口的沃约阿尼斯,其声誉却大大增加了。卡塔潘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亨利对此心知肚明:卡塔潘居住在普利亚,他可以一直维持、巩固自己的地位,还能毫不迟延地抓住任何机会去提高自己的地位。相比起来,西部皇帝只能通过他的封臣来行动,正如近期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封臣只有在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时候才会保持效忠。亨利在意大利时,他光芒夺目,控制法庭,主持正义,并且慷慨地赠予钱财;封臣们迫不及待地向他臣服,表示忠诚。亨利离开之后,该地便对不满者和煽动者敞开了大门。法律无人遵守,道德被破坏,禁令被遗忘。沃约阿尼斯不会错过机会。接下来要怎么做才能阻止帝国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体系再次土崩瓦解呢?
拜占庭人看着帝国的主人缓慢地向群山离去,必定长舒了一口气。如果亨利拿下了特罗亚,整个普利亚都会被他夺去。拜占庭人没有保住西部,这意味着过去4年的成果消失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重建。幸亏特罗亚没有失陷,拜占庭人的基础还在,因此希腊人的对外活动可以再次开始。毫无疑问,沃约阿尼斯重赏了特罗亚人。
因此,1022年的战役对两位主角来说都是没有结果的。很难不偏不倚地评价双方的得失,很难看出优势在哪一方。在那些卷进来的小势力中,卡普阿遭到了灾难性打击,萨莱诺和那不勒斯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在这一年的事件中,完全获益的只有一群人:诺曼人。由于他们站在特罗亚一边,为希腊人拯救了普利亚,所以获得了沃约阿尼斯的持续感激。在西部,他们在降伏卡普阿的活动中受到了亨利的奖赏,他委派诺曼军队来维护和帮助泰阿诺的潘都尔夫。其他的诺曼人被皇帝安排在拜占庭边境沿线,以及沿海防备撒拉逊人的各处地方。诺曼人事实上已经对下列方法尤为熟稔:站在胜利者一方,从胜利中获益,避免卷入任何失败。他们在半岛的东部和西部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对两大帝国而言都是不可缺少的。他们的确做得不错。
①按照他的标准是无瑕疵的,但是他必须背负一项耻辱,那就是在中世纪的罗马历史中第一次(虽然不是最后一次)以官方名义发起了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这是1020年的一次小型地震的结果。
②被选出的德意志国王只有在罗马得到教皇的加冕之后才可以使用皇帝的头衔。亨利也是第一位在皇帝选举时自称“罗马人的国王”的人。
③“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阱里。”(《圣经·诗篇》7:15)
④即特洛伊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