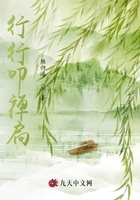
第17章 梨花酿⑷
不过还好我聪明机智勇敢正直善良,一下就避开了摆渡老翁那那艘大船,顺着水流的波纹慢悠悠地飘着。
这次不似上次,还有糊涂的摆渡老翁带路,也没有桨只有一下没一下的划着,没有人在后面盯着我,反而更显自由自在,我听着耳边滔滔不绝的江水,升成了一缕炊烟,托着腮欢快地打起盹儿,慢慢的,我也察觉到了丝毫的不投契:怎么跟黄泉关一样,无穷无尽?
我愤恨地往回看,但除了我这个魂魄漂泊,哪里还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暗暗操纵?
但面前出现的景观却让我大受震惊:
海啸夹杂着沙尘暴,以翻天覆地之势,向我席卷而来,我的瞳孔放大了几倍,却怎么也遮掩不住眼底的恐惧,这是还哪容得下多加思虑,赶紧逃得越远越好……
但很快,我就被这股神秘的力量打败了。沙尘暴不甘屈居人下,在海里兴风作浪,不禁嚼碎了摆渡老翁的船只,以至于也要把我吞没。
海啸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眼见着沙尘暴在自己的领地如履平地,恨得牙痒痒地跟上了她,一浪接一浪,一潮翻一潮地涌了上来,我提着裙子不顾一切地往回赶,这两人哪容得下这般戏弄,推着我就往中间的巨大漩涡拖,我见又要落水了,赶紧拖了身上里三件外三件,想让这些衣服不再拖我的后腿。
还是来不及!天上的雷霆已经轰隆隆地劈下来,我捂住头部顺势往下一跳,就在我落水的那一刹,一道闪电就这样击中了我,我浑身都失去了力气,划水的那双手也往下坠,紧接着,我便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已是鸟语花香。
我挣扎地从地上爬起来,摸了摸全身的衣服,才想起此时阳光正好,说不定早已晒干了,由于脱得只剩中单,说不定被人看光了,我盘着腿坐在地上,用树枝拨弄着地上的枫杨种子,仔细斟酌着历经此劫,到底收获了什么。
才开始遇见摆渡老翁纯属意外,他本想带我直接去判官那里,画上一笔直接投胎,没想到我误打误撞掉进了湖里,来到孟婆释迦的老巢。
鉴于我不明白死因,强拉着孟婆调查,孟婆只好与我缔结契约,一边指挥我卖忘忧水,一边暗地着手调查。她知道真相后却不告知我,也是怕我接受不了。
但细想刚才,分明是两个魔王在捉弄我!海上怎会起沙尘?沙尘又怎能越海浪一步?想想都荒唐。
但我被雷击,却是不关他们事。我的眼睛变成了这般模糊样,也是无可奈何。
既然回到人间,就该好好看看余杭小镇了,只可惜汴洲容不下我们三人,任峨眉怎么折腾,也逃不出命运的魔爪。
我现在是个睁眼瞎,只能勉强看清这是我与峨眉生前许愿的枫杨老树,枫杨树洞破旧,我摸着树干感受着枫杨仍在顽强生长着,它树上的种子几近干枯,但树叶却泛着鲜嫩的颜色,枫杨的脉络是清晰的,我却不数不清它有几圈年轮,只是一想到它是我和峨眉的特殊纪念,心里总有些难过。
枫杨的位置在一户无人居住的屋檐下,这里离古井很近,终年都是凉沁沁的,坪上长了芦苇,长久以来都是孩子挨了爹娘骂,除了家第二个庇护所。
汴洲踢蹴鞠的孩子长大了,有的在余杭小镇开起了店铺,有的成了要饭的叫花子,有的离开此地远赴天楚、千渚、平国做起了生意,有的则被当红的翰林记恨,发配到了边疆苦寒之地。
我听着院子里传来的犬吠声,想起来这户人家面前应该是有一小片竹林的,还有一条养着大鹅的溪流,经常有群孩子在这清澈见底的溪流里游泳,游累了便趴在大柳树上光着膀子晾衣服,现如今溪流早被填平,小小的院子围上了篱笆,种上了当季的菜品,小院里两三个妇女在织桑,满地爬的小孩乐呵呵的,有一勺没一勺地往对方口中送饭,画面既和谐又温馨。
我刚想走出这里和他们打个招呼,谁知阳光刚照到我的手臂上,手上的皮肤便发出滚烫的灼烧感,我痛不欲生地缩回去,含着泪正想问他们借瓢水淋一淋,可当我喊出声时,院子里的人却置若罔闻,只是都回头看了一下,看到屋子里的黑猫乱窜,主人家连忙拿起扫帚赶。
我正想拍打她的肩膀,可她穿过了我的身体,径直朝黑猫走去。
她真的看不见我?我一脸震惊,正想绕开他们乱蹦乱跳,刚想起来对阳光过敏。
我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广场上日晷指针随着光线的角度变幻,我蹲在地上数枫杨串串,不知不觉有了睡意。
孩子的嬉笑声已经渐行渐远,妇人们收起了缫丝,穿上围裙开始在灶房烹炸食物,煎鱼的香味从里间传来,干农活的男人们背着锄头,扎起裤腿准备冲洗身上的泥泞,一家人围着饭桌前,其乐融融地吃着晚餐。
我饿得肚皮咕咕叫,却只能眼巴巴桌上那点剩饭剩菜,吃饱喝足后,圆盘中留下许多鱼刺,男人们伸了个懒腰,便跃进妇人们准备好的木桶里,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
屋子里的声音已经笑了许多,灯罩里的烛光不知被谁吹灭了,薄壁里只能透出相依而眠的两人,呼吸声缠绵,池塘里的蛙鸣此起彼伏,月亮爬上枝头,小院里只有我在画圈圈。
午夜过后,打更人的小镲有一声没一声地敲打着,我在树上睡得正香,听到黑夜里这独特的呼唤,也忍不住起身飘下来看看动静。
我走到万人空巷的大街,内心居然有些害怕。我不敢回头看,那是因为常听孟婆唬人,说恶鬼常在夜里找吃食吃,他们见不着人的时候,就会拿路过无辜的魂魄开刀。
我把手放在身前,试图用手里提着的灯驱散黑暗,可雾气越来越厚,月光洒在树枝上,为那些枯瘦的枝干披上银色的披风,我仿佛听见四周有什么动物在叫嚣,我哆哆嗦嗦往前走,只等碰上个好心人。
十里春生已经封锁了,那是官差给下的通告。我悄悄溜进后门,才多了一份安心。
小院里的碗莲在清晖的照影下亭亭玉立,凌霄花饱受风雨的摧折,却依然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我鼓起勇气往我的房间走,过道里却随着我的走动而亮起一片灯火,我携一盏宫灯慢慢往里飘,大堂内立着的木牌却异常醒目。
——上面刻着的是我的名字。
吾妹谢氏秋娘之碑,这几个字印在我得眼前,始终挥之不去。
我的左眼流下了一行清泪,只可恨右眼干涩。木牌之上还带着残留的血迹。不知为何,看到峨眉生前还能有一丝悔恨,我明知她犯下的罪孽不可饶恕,却念及这来之不易的感情,突然很想原谅她的所做所为。
若没有恶鬼的驱使,她是否会诚心悔过?这个答案在我心中,似乎也跟孟婆的话如出一辙:死后不也如一张白纸烟消云散吗……
是的,这个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十里春生的茶具上落了灰,我也无心去擦拭了,只是看着它一天一天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从人们的耳中隐匿,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我真的很想把这里整理成开业的模样,可一拿起木椟刻字便掉落在地,一拿起盛花生米的小碟,便‘碎碎平安’了。
马头墙上竟坐着醉意醺醺的少年,把手指含在嘴里,睁大眼睛看向十里春生茶馆,院墙内的我,被灯光映照的脸格外阴冷,特别是身上那些素衣……
我正欲解释,他却翻身不见了。
院子里留存着熟悉的一切,可终究物是人非,我眷恋地看了最后一眼,强忍住伤怀的情绪,躲到树上偷偷抹泪去了。
第二天,晨。
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缓缓洒落,枫杨上栖息的麻雀也逐渐活跃起来,院子里有了生机,小孩哭着闹着揪着男子的短褐不肯上学堂,妇人一脸愁容地站在门槛前,在门簪上抓下一道抓痕,恨不得马上就背起孩子往学堂的方向扛。
我最终还是被他们闹醒了,昨日夜游茶馆的亲身经历还历历在目,只是麻雀大概是嫌树上太寂静了,竟往我的天灵盖洒白豆子,白豆子湿湿滑滑,问题就是阳光一照,根本抹也不掉。
要不是早已化身魂魄,看到有鸟往我头上下白豆子这一幕,真相立马爬上树与这些不讨喜的麻雀决斗一番。
天上的云来了又走,只可惜这么大的太阳,还没等把被子扛出来晒,倏然一下子转阴了。
远处的锣鼓,铙钹声吹得耳朵有些发疼,我刚想开口骂这是谁家不看黄历迎娶婚嫁,但抬头望了眼街上,披桑戴麻的人却不少,孝子走在最前面,四名轿夫抬着沉甸甸的桃木棺材,后面哭丧的孝子贤孙成群结队,住在附近的捧个场面,一路提着竹竿放爆竹,一路提着篮子洒纸钱。
我感伤地避过头,但耳边锣鼓喧天,却这么也遮盖不住。漫天的纸钱随风飘扬,落在轿夫的身边,落在路边的小摊铺面,阴云密布的天,空气中还裹挟着雨丝,我的脚不受控制地往外飘。
大概是受引灵幡的影响,我就这样慢悠悠地飘进了灵堂,看到那还没有结束的丧礼,吹二胡,唱悼词的一个起劲,跪在草席上的还在烧纸钱,火光映照在他们憔悴的脸上,那双凹陷的双眼依旧铁青,面上泛起乏力,长跪不起的膝盖已失去知觉。
我只觉木牌上的名字熟悉,却如何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后来我从阎王的《生死备忘录Ⅸ》里偶然看到最近逝去的人们,才得知这是没事来后院坐坐给我们送桂花糖的钟婆婆,婆婆是个孤寡老人,平常很少见她笑,我们也没什么报答她的,她尝不了荤腥,等等就只能炒几个小菜一起聚一聚,婆婆也从没开口提过人情是一物一图的理念,只是生死离别在所难免,想不到身体一向健朗的钟婆婆,就这么在睡梦中离去了。
其实寿终正寝才是最不错的选择吧!人生在世都会承受许多疾病,有人天灾,那就有人祸。相比于这种苦痛的离去,多数人更希望像钟婆婆这样吧。
丧宴上来来往往,他们的眼泪掺杂着真情假意,钟婆婆的几个女儿都成了亲,这明里说不得的便是要分上一杯羹,身前没有好好孝敬,生后也是举行简单的仪式感,再比如说平常和婆婆交谈的人不多,有邻居想随个份子的,便有凑个热闹看清闲的。
我突然联想到自己的丧礼,这时我已经没有任何意愿去怪峨眉了。尽管她与我的死脱不了干系,尽管这一架后等等发配奴籍,可无无时无刻还是会想起在人世的那些美好。
倘若我的丧礼也如此浩大,那真是谢天谢地了。外面这些宗亲很奇怪,总是设法站在利益的角度剖析问题,就比如我家属于谢家的一类旁支,是不能上主祠堂的,可是一到算账,这些人就全都像啖肉的狼群一样围上来。
我不知峨眉是如何应付的,反正给他们吃瘪后,他们就再没来过十里春生茶馆,茶馆冷清清的,早已被人遗忘在角落,倒是远在开屏的爹娘,不知道身体是否康健。
我看着丧礼散场。宴席之后,主家开始打发大伙清理礼堂。灼烧过的火盆黢黑,里面还盛放着冷却的纸灰,木牌还在,只是熏得有些着味,大家肿着桃花眼,打了个哈欠准备起身补觉,一餐荤素搭配的晚宴,明明是精心准备,但胃里却填充不了任何的食物,此时美味佳肴摆在眼前也索然无味,只是灯光似乎不像之前那么惨白,人间烟火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占领高地,成为最平常的琐碎现象。
人们慢慢过上原本的日子,小孩还是拍掌躲在大树下跟伙伴捉迷藏,男人们把稻田的水放掉,给这个炎热的夏日降降温,女人们都闹着要摘山里采桑葚,又是一年好时节,瓜果时蔬都已在菜地里长成了最初的模样。
我惆怅地离开这里。并不是无处可去,而是天下之大,根本容忍不了我们这些随处可能会消失的魂魄,一路上我已经听说好几处恶灵作祟了,我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是还是想提醒未曾谋面的黑白无常,要多注意异常情况。
夜里变了天,枫杨的叶子落了一地,我暗自庆幸,身为魂魄最爱滋养万物的雨了,于是这样想着,便睡着了。
天空乌云压顶,起初只是一两滴雨滴落在我的臂膀,毛毛刺刺的感觉让我冰凉,我并未在意,沉沉的进入了梦乡,我本来枕着树干睡得老香,但起了一阵大风后,我就扛不住了,轻飘飘地飞上了高空,不知身在何处。
还没等我降落,一只长着长臂,四肢弯曲,浑身绿毛,尖嘴猴腮的家伙便冲了上来,她两颗尖牙暴露在外面,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双眸呈琥珀色,在这幽暗深邃的夜空好像是点缀的明星,她伸出爪子划向我的那一刻,我准备侧身躲过,但她的爪子还是划破了我的脸,我摸着失去痛觉的半边脸,一道不小的口子正汩汩留着血,由于重力作用,我降落在一颗老树的枝丫上。
老树枝繁叶茂,这会赶上三更半夜,便惊飞了安居在树上的鸟儿,我吃痛的纠正了自己的腰,坐在枝丫上像骑牛,正当我开头骂“是哪个不开眼的恶鬼打扰本姑娘的美梦”时,林立的铺面前,却出现了一对双胞胎,穿黑衣劲装的少年戴着高高的帽子,手上拿着一柄拂尘,穿白衣劲装的少年腰上系着鼓鼓的钱袋子,手本本分分地放在身前。
我撇了他们一眼,也不知如何心中憎生了莫名的恨意,我总感觉他们并不是好人。一眼过后,我的注意力便被那袭击我的,在树上一蹦老高的猴子精吸引了,她的毛发浓密,鼻子不串气地时不时哼哼两句,我对她也可谓是没什么好感的。
只见两人站在那里,嘴唇蠕动着,但听不清说了什么。我用孟婆的咒法小小施用,这才不用辛苦读唇语。
这位叫黎塘的黑衣少年脾气暴躁,脾气显然不太行,指着那个在房屋上行走的猴子精,便破口大骂:“你个老山魈,别以为你在人间我就抓不着你,这些天你是越发猖狂了,不仅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壮年男子,连尚在襁褓的婴儿你都不放过,果真是无情无义。”
原来这只猴子精是只山魈啊,我仔细端详着两人,貌似两人年纪不大,估计是英年早逝,他们俩应该是阎王派下人间的无常吧,正常避开他们就好了,不过我与这只山魈,哦不!恶鬼附身的山魈,也算是结怨了。
山魈冲他们龇牙咧嘴,见打不过两位鬼差,便躲在人间肆意妄为,这下又在人间屋顶上闹,我预算这两位是不会放过她的。
我躲在树上无人察觉,心里偷着乐。骑在这个树上不好观察,索性我就拨开叶子,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们。
那山魈洋洋得意,欢快地在屋顶上跳来跳去,白无常生怕她把人家的屋宇震塌了,到时候他们还要化身夫妻,说自家孩子不懂事,砸碎了还要赔礼道歉,刁难一些的说不准会把口袋掏空。
黑无常却不在意这样,尽管激怒了是自己,也要先杀山魈泄愤:“臭山魈,看我不先你收入锁麟囊!”
说话间他已拔过白无常腰间的钱袋子,准备施展法术教训一下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山魈,白无常却拍拍肩,还没开口劝住她,那山魈的脚程便按天下第二算,没人敢称天下第一:“黎氏兄弟,本姑娘就不陪你们玩了,改日再回。”
她的声音嘶哑嘈杂,如我碰见的那些怪物一般阴险狡猾,只是我没想到,黑白无常追踪这么久的山魈,竟是女子形态,我暗暗不屑,想不到名声在外的黎氏兄弟,竟然啥也不会。
眼见那山魈要跑,黑无常急的脸都憋红了,只一个劲儿在那里干着急,白无常拍了拍,深沉的摇摇头,那张看不出任何表情的木鱼脸却仿佛在说“万般皆空”。
等到山魈走后,黑无常气的牙痒痒,恨不得把那只女山魈剁成快,把拂尘好好鞭笞一顿,白无常的第六感却不差,他好像感应到我了,余光有意地往我的方向望去,我屏住呼吸争取不看他,但好似只是恍惚,然后继续和黑无常聊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