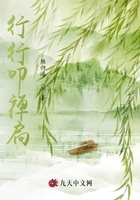
第23章 梨花酿(9)
岳明朝望着头顶的月光,心里一阵凄然,他在何今夕身边就这么默默陪着,一步也不肯挪动。
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浅浅的哀愁:“今夕,我对不起你,从一开始我只想让岳家在龃龉村出口气,谁知氐国暗探竟以举家性命相要,我迫不得已才为他们办事,所幸他们要的只是前朝往事,不是军中机密,今夕,我知道自己出卖国家不对,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他温柔的哄着何今夕,但何今夕还是抽泣不止,显然已经了解他的套路。
“岳明朝,你为了与自己开解,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她仰头看着岳明朝,臂膀自然地放在双膝上,她已经对岳明朝彻底失望了,语气中带着刻薄和怨恨。
岳明朝不说话。
“岳明朝,放过我吧,也放过你自己。”
何今夕泪痕淡去了,她头脑空空,什么也不想,带着微笑在一片纷乱的杏花雨中离去。
岳明朝奋力想抓住她,却发现自己也腾空而起,消失在万人空巷的龃龉村。
故事又回到了最初,他们相遇的那个春日。
那是癸卯年,岳明朝的本命年。
垂髫小儿倚靠在窗边,静静地看着支起的窗格外,飘着的斜斜雨丝,粗糙的杏树上,胭脂色的花朵藏在枝丫间,落了一地的芬芳。
外面新鲜的空气灌进来,可他的心里还是闷闷的,屋檐下的雏鸟啾啾的叫着,青石板铺地湿淋淋,连屋子里的书画都长了蛀虫,不出阳光的日子很难受,心绪也总是会被东一阵西一阵的雨所左右。
屋外响起了有力的敲门声,侍女环佩伸着脖子,悄悄地瞧自家的少爷,岳明朝唇红齿白,眉眼弯弯,模样虽然略带稚气,却依然掩盖不住骨子里的英气,简直就是岳老爷的翻版。
环佩见到少爷心情极差,自然也想哄好岳明朝,于是挤了张笑脸,谄媚道:“大少爷,今儿个老爷从外面带了个标致丫头,您要不要去外厅瞧瞧?”
岳明朝撑着下巴,头缓缓扭过来,慢慢悠悠地说道:“能有多标致?这世间的女子千千万,不过都只是会顺从他人的心意罢了。”
环佩“噗嗤”一笑,试图想逗乐他:“听说那丫头是岳老爷捡回来的,这丫头能读书识字,想必是大户人家出身。”
岳明朝听罢,顿时来了兴致:“那丫头多大?可会识文断字?”
环佩有些不确定,但还是不敢把心中的猜想说出来,只是迟疑地说道:“跟您差不多年纪,至于会不会识文断字,奴婢就不清楚了,您要不要亲自去前厅看看?”
岳明朝“噌”地一下起身,拨了拨香炉上的铁盖,盖中的焚香便以微妙的角度曲折下来,随后凋零败谢。
烟雨朦胧中,岳明朝支着油纸伞,行走在铺满鹅卵石的花园小径,狗尾草沾满露水,便轻易将衣袂打湿,那叫做环佩的丫头昂首挺胸,没有太大的步伐,只是老老实实跟在少爷身后。
两人走得很快,环佩举伞虽巧妙,没让岳明朝淋湿半点,自己半边肩却以浸润。伞面很大,雨水便轻盈地顺着伞骨滑落,点点滴滴,促使水边的鸢尾袅袅婷婷。
到后院到前厅要经过一个回廊,那是唯一避雨的绝佳场所。只可惜岳老爷对百姓比对自己家里人还要热切,不舍得在上面下真功夫,要是再修剪一个凉亭,或是放在几个石墩,也不至于回廊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
他们到那里时,还是晚了一步。前厅空荡荡的,除了垫茶的桌布,什么也没有,桌布上还有余温,人应该是才走的,可惜服侍岳夫人的丫头粗心,逐渐冷却的茶拿走了,只是洇水的桌布还在。
正当他失落地打算折返,后山中传来了剪刀的“咔嚓”声,他愤怒地赶上前,正准备驱赶雨中裁枝的小偷,却看到:雨中有一个双髻扎着两根红线的小女孩,她把薄如蝉翼的油纸伞夹在油纸伞,穿着丹樱色的齐胸襦裙,粉白的小鞋在泥泞中艰难移动。
凑近一看,她的手里拿着一把大剪刀,腰上的篓子却装着几支比她高出一点的花枝,女孩瘦弱矮小,武起园丁修剪枝叶的剪刀时却丝毫不弱,尽管杏树高大,花枝密集处连攀梯都无法企及,她掂掂脚却只裁近处的花枝。
他顿时痴了,向身后的环佩使了个“嘘”字,便一个人踏上了乱石打磨的平台,走进迷人眼的杏花林,女孩察觉到身后有人,默默躲进花丛里,拿着手中的剪刀不知所措。
她额前的流海随之打乱,女孩怯生生地用杏花遮掩,大概是第一次见到比她高的男孩,她的脸竟红成了猴屁股,一时结巴:“你……你是谁啊?”
岳明朝仰着头,高傲地回答:“我,是将来这杏林的主人,岳家的少爷岳明朝。”
小女孩眨着眼睛,迷蒙的眼神像初开混沌的盘古:“你就是……岳老爷的独子?”
岳明朝高昂着头:“你是阿爷带回来的丫头吧,你叫什么名字?为何私自来杏园折枝?”
女孩向他请安,有些委屈地嘟着嘴:“散会后,岳老爷让我四处走走,适应一下环境,以便未来在府上行事。”
岳明朝点点头,算所有表示。
女孩又道:“我叫何今夕,《二灵寺守岁》里‘不知今夕是何年’的今夕,岳老爷说,我是你未来的妻。”
岳明朝扼腕叹息,到底是阿爷没教好下人规矩,还是这个叫何今夕没听懂话……
算了罢,就让这个美丽的错误延续吧!
岳明朝不想再计较那些,伸出一双手来,轻声道:“今夕,你下来,我接住你。”
何今夕眼中有两泉汪洋,看着他温柔的眉眼,在花雨中迷离,她心一软,便将手递了过去。
岳明朝抱了个满怀,杏花扑鼻的香味袭来,吹开了两人的衣襟。仿佛在这定格一瞬的深情对视间,一句轻飘飘地“跟我走”即是永恒。
殊不知,这场意外的怀抱早已预谋许久。
“守岁山房迥绝缘,灯光香灺共萧然。
无人更献椒花颂,有客同参柏子禅。
已悟化城非乐界,不知今夕是何年。
忧心悄悄浑忘寐,坐待扶桑日丽天。”
袅袅的歌声仍在继续,而故事中的人早已烟消云散。
囊中的岳明朝久坐醒禅,睁开眼正想追上记忆中的女孩,抬头一片陌生,何今夕却早已消失在人群之中。
外面的天地,已是日上三竿。
黑无常拿着从破庙里捡的棕扇,有一下没一下地借助扇骨扇着风。天气非常的热的时候,狗都趴在水沟里吐舌头,人更受不住了,有条件的还可以躲到地下酒窖乘凉,没条件的赤着脚摇摇晃晃地走在街上,直接倒在人家屋檐下。
白无常不紧不慢地走着,仿佛“心静自然凉”真的不是口头上所说的俗语。实际上他也是有点私心的,那就是偷偷在衣袍里藏东海龙王送给他的千年玄冰,龙王说越深的海水越彻骨,白无常暗暗感慨,果然冰山下的一角所言非虚。
那时我躲在瓜田旁的小屋里,偷吃上贡给土地神的的西瓜,西瓜汁沾得到处都是,悠闲自在的我尚未感受到危险到来,刚咽下一粒粒西瓜子,旁边蔓延的藤蔓就一把把我的四肢缠住了,我欲哭无泪地吃完最后一口瓜,紧接着就被藤蔓拖出了屋外。
两尊瘟神面不改色,黑无常见我嘴上还蘸着瘪了的西瓜子,差点没笑出来。
白无常一本正经地打量着我,头顶上高高的帽子,在太阳的折射下展现一道光晕。
我还没开始辩解,黑无常就已经按捺不住了,抽出腰上的鞭子,劈头盖脸地甩向——我身边的地?我双手掩面,还没见到更为血腥的一面,先吓得花容失色了。
那黄土地泛起漫天的尘灰,未熟的西瓜只能深夜流泪,到底为什么……要伤害帮我们传播种子的女巾帼?想不通啊想不通。
“之前太过放纵你,是因为还有要事在身,如今清闲了却不得不多嘴一句,”白无常缓缓启唇,恐吓道,“在我们的领地,偷吃同类可是要进十八炼狱走一遭的——”
我下意识往后缩,不料手碾到一个小石子,手心顿时溅起血花。
白无常见我面色惨白,嘴角划过一道可怖的笑:“嘶——想必你还没有见识过我们的手段吧,今天正好让你开开眼。”
他已然从衣袍里拿出一个装药丸的葫芦来,一把拧开葫芦塞,弯腰对我说道:“这本来是用来装恶灵的葫芦,如今闲着也没用,不如让你进去玩玩,待到血肉之躯融化,便化作醇厚浓郁的酱酒,让我们兄弟二人喝上一口……”
黑无常拍了拍他的手臂,不耐烦地说道:“还跟她啰嗦什么,入完十八炼狱直接请十王定罪,下辈子变成什么就不由自己决定了。”
我摇摇头,决意要远离逐渐变态的黑白无常,可我的嘴巴像是被什么堵住似的,一句“救命”都喊不出来。
正当此时,一道强烈的肃杀之气铺面而来,风席卷着漫天飘飞的瓜叶,在半空落定,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却发现上次救我的黑袍男子又出现了,他悬在巨大的龙卷风中,暴怒地说了一句:“还不退下!”
黑白无常随之向他问安,自此便隐匿了。
一根红绳再次缠住我的腰,我正庆幸没被瓜田捆住,又苦恼于这根并不结实的红绳。只见红黑相间的红绳束缚住我,黑袍男子脚下生云,裹挟着我便往空中带,本以习惯在地面攀缘,现在又当了半仙,自然吓得不敢动弹。
我被吊在空中拖曳,突然有股神秘的力量将我往上一拽,我的眼珠子突突直跳,耳朵里也灌风,等到终于开始匀速飞行时,他却质问:“给你七天时间,为何还不速来地府报道?”
我悬着的半颗心已经卡到了嗓子眼。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着,微微侧身:“莫非是找不到入口了?”
我还是没能回答。
他似是自言自语,神情中带着哂笑:“哦,我忘了,是本王的下属戏耍的你,不过人间千百年,都是一个模样,从来都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地方。”
我正想反驳他,却看到他身体前倾,他轻笑道:“去往地府的路十分艰难,这一路,你可要抓紧了!”
我还没做好准备,却被一阵迅猛的疾风带过。
随后,我听见迅雷在催打,狂风在呼啸,紫电闪过,乌云堆积如山,我的发箍不知被吹去哪了,披散着头发脸上两团腮红,身上的素衣已变成囚衣,而我搂着黑袍男子的腰,闭着眼在云中疾行。
不知过了多久,我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睡着了,据后来阎王本人反映,他把我拽到胡床上吐槽了一句好重,我在小小等我胡床上打起了呼噜,他施用法术换完衣服便先行离开了。
反正醒来后,我看着头顶的骷髅头,差点没找个地洞藏起来。
书房的烛光很暗,加上本身我的夜视能力就不是很好,摸着黑翻到了一盏类似于青铜器的树状灯柱,脚下好像有凉意沁来,我正打断挥手点燃这十里之外的烛光,不料碰到一些类似于竹简的东西,衣袖一拨便哗啦哗啦掉落在地。
这时,石门的翕动发出,我慌忙地从地上捡起这些竹简,一块,两块,三块……黑暗中有双手却弯腰拉住了我,我脚下的裙摆一拉,“碰”地一下连带着人滚了好几圈,男人闷哼了一声,唇齿生寒,貌似有人还在黑暗中舔了他一口。
呼吸并没有纠缠许久,一片昏黄的烛光擦亮了黑暗。
我看着周围逐渐清晰,抚摸着刚刚那股辛甜,久久地注视着那双面具之下的黑眸,黑袍男子正发出凝重的喘息,嘴角还带着若有若无的铁锈味,让我不知不觉想贴近。
难怪我……一开始就冒犯了人家?
我仿佛五雷轰顶般,注视着与我对立的黑袍男子,讶异得说不上话来。
但他只是淡淡一瞥,便边弯腰捡竹简,边默默地收拾书架,问:“你怎么做到把生死簿全扫落在地的?”
我摊摊手,表示自己对这个事一无所知,本来我只是想出去转一转,这倒好,反被人家误解了。
他低头整理着书卷上的东西,合上文书与关碟,认真用抹布擦拭着桌面,突然来了一句:“你有没有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我摊摊手,解释像极了掩饰:“我可没有啊,摸黑还能看到什么。”
接着,他努力地想从我的黑眸里看到什么,但是我极力的掩饰,包括手背在身后揪着衣角不松手,以上皆为我的想象。
然而他只是不置可否,裹挟寒霜的笑意在唇齿间漾开,我看他露出了两颗的虎牙,不禁脑补这个大魔王,摘下面具后会是怎么一番模样?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戏楼里说书先生对美男的描述:人神共愤?喜形于色?儒雅风流?还是绝世无双?
关于面前这个男人,挺直了腰杆站在我面前,我划分了一下比例,却怎么也够不到他的头。
正当我神游之际,他却从那开合闭落的八张石门中隐去了,回音中还带着丝丝的威胁:“你先待在这里不要动,我去判官那里给你报个道,随后便正式成为地府的行政人员,每月从一吊钱加起。”
我冲空气做了个鬼脸,便百无聊赖地翻起书来,一摞一摞是那么的厚重,些许是因为他的警惕,让我对那堆摆在桌案上的册子心有余悸,害怕会受到他的责罚,所以这些是决计不能动了。
我卧在那张又大又软的胡床上,嘴里还衔着阎王办公用的生辰笔,浑然不觉已经过去了几个时辰,等到我稍微有了点睡意的时候,那八张门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我一下精神亢奋,撑着眼皮就往外走。
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顺着那声音最近处听,随手抓起一本书,就悄悄地打开了一扇门。
好家伙!一听不知道,一看个个都是厉害人物。
——小小的方桌上,坐着四方着不同颜色的衣裳,有的髯须垂胸,有的胡子拉碴,每个人眼睛死瞪着,像极了一动不动的金鱼,旁边还有七人纷纷围观,有的坐在矮几喝茶,有的用着糕点,有着捻着盘里的瓜子看热闹,有人干着急。
由于光线较暗,一堆人围着并不知是在干什么,只觉得声音嘈杂,听得耳朵疼,我眯起眼仔细瞧瞧,才发现一脚坐着黑衣男子,这次他没有戴面具,脸白白嫩嫩的,神情老不好了,跟人欠了他十万八千似的。
我朝他的方向翻了个白眼,鬼点子瞬间就从脑海中冒出来了。先是变出一壶酒,再加上几个杯,我拿着托盘,化身于侍女的模样,看了看自己美艳的指甲,哎!可惜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蹑手蹑脚地走进那一间房间,先是四下逡巡着布置,从天花板到窗户,从景物到人物,我一样没放过。本来碰到这么多人,还不敢兴风作浪,但是一想到这群扰人清净的地方官,一个个都是坏角色,不如把那些在十八炼狱折磨得还剩半口气的魂魄的仇报回来,也值了!
我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张望左右发现他们都在专心致志做着自己的事,这让我胆子壮了不少,细看那四人抓着的四张牌,黑红相间,点数分明,桌上的骰盅揭开,显然是大小不一。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牌九?
看他们嘴里念念有词,我也入了迷,站在旁边倒酒,不知不觉溢满了杯,我身边的绿袍汉子看不下去了,连忙端一饮而尽,不耐烦地叫我退下。
这么多人在场,总有几个爱出风头的,坐在那里剥花生的紫袍汉子磨破了花生皮,招呼我过来:“你怎么回事啊?倒个酒都磨磨唧唧的,严崇明你什么时候招了个丫鬟?”
这个叫严崇明的男子扭过头来,而我蒙住眼睛,用透出的光琢磨着黑袍男子,他并没有发怒,只是和才见面时那般冷漠无情:“七王误会了,我与这丫头片子素不相识,哪里谈得上指示?把她拖出去吧,这样本王就不用亲自跑一趟了。”
我瞪大眼睛准备跑路。
大家都没见到阎王第一次说这么多话,纷纷引来瞩目的目光,也瞬间读懂了阎王是在调侃他的下属。
我反而失了分寸,端起托盘就要往八个不同方向的门跑。
但由于我不记得从哪扇门出来的了,所以迟迟伫立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