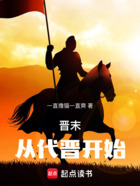
第10章 谢琰募兵,击鼓鸣冤
“你侄袁成正在大狱中,我之爱将亦是如此。以这谢混强势霸道脾性,想必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我们得救他二人。”
桓宝缓缓说出心中想法,尽管他此前将句章当做自己的一言堂,袁崧这太守毫无存在感可言。
但此一时彼一时。
有句话叫——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袁崧当然想救自己的侄儿,只是多年为官生涯,令他比较能忍,于是不动声色地问道:“桓将军觉得,该如何救?”
桓宝没有在意袁崧的作态,他凝望郡府前的百姓,意有所指:“既然谢混在意民心,那我们便好好用这民心。袁太守...咱们边走边说...”
...
郡府中,谢混正在接见闻讯赶来的刘宣之。
本来作为上虞驻将,未接到军令,不该擅自离守,但谁让谢混是顶头上司的儿子呢?
他收到桓宝的密信后,就一直关注着句章情况。
直到昨日下午,句章一封飞鸽传书,得知孙恩即将叩城,他急忙率领三千人,连夜冒雨急行军,于下午赶到句章。
刘宣之抱拳,声音洪亮地恭维道:“谢长史,恭喜大胜!末将佩服!”
他与桓宝不一样,是谢琰举荐的谘议参军,属于亲信将领。
桓宝是受朝中委派,来协助谢琰镇压叛乱,一旦孙恩等贼寇俯首,他便会离开三吴。
谢混亲自上前,虚扶其臂膀,微微一笑:“不敢当,将军于三吴驻防弥久,与贼军大大小小战斗数十场,皆无败绩,本长史亦深感佩服!”
当爹的怠慢这些武将,他当然得收敛人心。尤其是谘议参军这种,天然亲近主帅,只要肯用心待之,迅速就能建立亲密关系。
此前的亲卫军都督张猛,其实比刘宣之更容易亲近。
可惜谢琰自视甚高,不把人家当人看,令其心生怨恨。
对于谢混的举动以及说的话,刘宣之很错愕。
他断然没想到,会受到如此礼遇和赞扬。
虽然最近谢琰改变了不少,对他们这些将佐属官客气不少,但人是有记忆的,与之前谢琰的举动相比,谢混这种刚接触便以礼相待,着实令他印象甚佳。
不禁感叹:同样是姓谢,两父子为人差别,咋这么大呢?
当即抱拳深躬一礼:“长史谬赞,此乃末将分内之事。”
谢混微微一笑。
要不怎么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大部分冲阵杀敌的武将,脑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谁对他好,立刻就能得到反馈。
文臣则不会,权衡利弊、勾心斗角是他们的天性。
再次将刘宣之扶起,谢混没有继续煽情,凡事适可而止,用力过猛反而会弄巧成拙。
刘宣之想了想,询问:“谢长史,先前我收到桓将军密信,在上虞郡收押了一批士族,您看要怎么处理?”
处理上虞士族的事,他其实应该向谢琰请示,不过既然谢混更好相处,又能代谢琰行事,当然是就近选择了。
听他这么一说,谢混倒是想起句章也收押有一批,当即让人去叫来桓宝。
得知是关于收押士族的事后,桓宝说道:“谢长史,我正要向你禀报,那两家士族都已招了,确有人勾连孙恩,欲为其提供便利。”
“甚至这几月来,孙恩在海上的用度,也有一部分是他们贡献。”
刘宣之也赶紧补充:“上虞的几家也是如此。”
他收押的陈氏、萧氏、胡氏中,有一个软骨头,刚上刑就吓得粪尿齐流,当场招供,要比句章的刘氏、谭氏好审。
对这种贼寇同党,谢混并未处理过,他沉思了一会儿,给出了自认为比较合理的处置。
“这几家士族,所有参与的人,押往会稽,交由谢内史处置。涉及人员的三族亲属,全部严加看管,服徭役五年。其余无关的人放回家中,派人暗中监视。”
交给谢琰的人,不用说,肯定处死。至于其他人,罪不至死,
原本他还想在这三吴来一场清洗,毕竟太祖有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些隐藏于士族中的孙恩同党,远比那些愚民信徒,威胁性更大。
不过想到还要引导孙恩去攻丹徒,便暂时放弃。
若是把这些外援全搞死了,到时孙恩实力不足,不敢去,或者去了却被刘牢之干掉,那就得不偿失了。
...
会稽郡,乡野之间,两佃农正在田中劳作。
一名佃农边翻土,便随口闲聊:“听说了吗,谢内史发布政令,要再募集一万兵众,抵御孙贼。”
另一人知道的更详细一点:“当然知道,前几日,孙寇聚集两三万人袭击句章,被谢长史打败,谢内史觉得,贼寇下次来犯必会更加声势浩大,这才招人。谢内史还说,贼寇祸乱,百姓流亡无家可归,因此主要招流民、乡勇,以解生存燃眉。”
“原理如此,谢内史真是体恤我等庶民。对了,有传言袁郡尉、严贼曹,被下大狱了。听说,两人是好官,帮助过不少民众。”
“有这事?既然是好官,为啥还被下狱?”
“这倒是不知...”
...
对于谢琰招兵的事,谢混也收到消息了。
他倒是觉得才招一万人,太小气了,起码得三五万,再从中筛选良种,训练成精兵。
不过时间还长,一次不够,就招两次、三次,总能把人凑齐。
倒是流传的另一条消息,很有意思。
谢混为自己续了一盏热茶,又给刘穆之递去一盏,问道:“穆之,这袁成、严民的事,你如何看?”
刘穆之道谢后,恭敬接过,轻呷一口,缓缓开口:“主上,你命督邮陈昌将二人下狱后,我特意调查过他们。据我所知,这两人往日并无仁举,此番流言,应是有人故意为之。”
谢混恍然大悟:“哦,我还以为抓错好官了,说说他们的情况。”
他之前一直忙着熟悉事务,后来又筹划备战,暂时抽不出时间,了解这些下层官员。
刘穆之能先他之前,考虑到这些事情,确实很用心。
“这袁成不学无术,之所以能当上郡尉,只因袁崧是其堂叔。在任期间,也是整日玩忽职守,时常不见人影。”
“严明原为句章城中小吏,半年前桓宝来此地驻防,偶然间投入其麾下,成为亲信,这才被提拔。此人甚是油滑,在升任贼曹掾史后,鱼肉百姓,欺男霸女。”
听完这两人的具体所作所为,谢混不觉得意外。
关系户,哪个时代都存在。
只要上面有人罩着,胡作非为、贪赃枉法简直家常便饭。
升官。
能力只是极小因素,关系才是硬道理。
泱泱华夏几千载,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人,还少了?
“如此看来,这手笔是出自咱们的袁太守、桓将军,妄图以民舆逼迫我,将两人放了。”谢混冷笑。
这是见自己体恤百姓,所以想从舆论入手,实行道德绑架,逼他就范。
只要这次让他们得逞,以后这民舆便是两人手中的刀,随意拿捏他。
“穆之,立即去收集二人罪证,我倒要看看,袁崧和桓宝究竟想干什么!”
见谢混动了真怒,刘穆之明白他是想法办两人,有些担心到时会与袁、桓起冲突。
他沉思片刻后,郑重询问:“主上,需不需要再收集几人之间有无牵连,顺便让蒯恩他们随时戒备?”
“如此最好不过,有备无患!”
...
句章城大狱中,被关押着的袁成、严明,正一边大块朵硕,一边吹牛闲聊。
“严兄,我二人倒是同病相怜。那姓谢的,揪着暗道之事不放,居然将我们革职下狱,简直小题大做!”
说完,袁成狠狠啃了一口鸡腿,大嚼着,顿时满嘴流油。
“袁兄且把心放到肚子里,桓将军和袁太守已在为我二人奔走,想来不日便能出去。”严明胸有成竹,对自己的处境丝毫不担心。
袁成只是发一下牢骚,堂叔在为他谋划之事,他也知道。
那姓谢的虽为长史,但郡太守加广武将军的影响力,不可能不顾及。
很早他就明白,江湖、官场从来不是喊打喊杀,讲究的是人情事故。
今日你给我留面,明日我给你抬轿,这才是皆大欢喜的场面。
“这我倒不担心,只是进来之前,那姓赵的小子,一直在堵我家门,就怕到时...”
说到最后,袁成有些心虚。
闻言,严明放下手中筷子,左右看了一眼后,见狱卒离得远远的,这才一把抓住袁成衣襟,恶狠狠道:“我不是让你把他做了吗?!”
他跟袁成臭味相投,平日里关系紧密,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两人都有份。
“我...我...”
袁成不敢对视,心里又觉得憋屈。
这严明庶民出身,跟他这有背景的士族子弟,天差地远。
只是走狗屎运,攀附上桓宝,这才能与他同桌而食。
搁以前,此人给他舔脚都不配!
“我尼玛我!马上给外面传讯,去把人宰了,处理干净。不然到时候不光我二人跑不了,还要牵连桓将军!”严明压低声音,警告他。
袁成不敢违背,慌忙点头,也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
经过几日酝酿,句章城逐渐出现请愿声。
有那茶摊边的说书人,称颂袁成、严明乃体察民情的好官。
有街谈巷语,宣扬二人仁义事迹。
还有甚者,要为两人请万人血书...
这一日。
郡府门外,忽然有人敲响登闻鼓。
“咚!——咚!——咚!——”
一声又一声,经久不息。
两名家奴模样的人,领着十几个庶民百姓,跪倒在地。
口中不断喊道。
“恳求谢长史,放了袁郡尉、严贼曹!”
“袁都尉是冤枉的啊!”
“严贼曹是好官啊!”
小吏拿着这些人毫无办法,不敢打,不敢赶。
只因武帝时期立制,击登闻鼓鸣冤者,不得阻拦。
郡太守袁崧立即将这些人迎入府堂,还特意允许百姓们进府围观。
他今日要做一回青天大老爷!
啪!一拍惊堂木。
“堂下何人?击鼓所为何事?!”
十几个人列排跪下。
“草民张二,来为袁都尉、严贼曹请冤!”
“草民王五,同来请冤!”
“草民...”
...
末了,一人拿出一张摁满手印、指印的白布,边向围观百姓展示,边说道:“袁太守,这是诸多民众的血书,还请太守您过目!”
挤满府堂的百姓中,传来一声声惊呼。
这东西,多久没见过了?
当然,有知晓内情的,脸上不屑一顾。
袁崧查看完血书,又装模作样询问一番,完成既定流程,当即派人通知谢混。
等谢混带着刘穆之来后,十余百姓立即转头,跪到他面前,为袁成、严明伸冤求情,并诉说两人的仁迹。
耳边被这些人吵得嗡嗡作响,谢混伸手喝道:“停!一个一个来,你,就你,从你开始说!”
被指到的人,缩首缩脑开始讲述...
接下来。
其余人又一一诉说。
总之,翻来覆去,就一句:两人冤枉,快放了他们。
等谢混听完后,掏了掏耳朵,又瞄了瞄那血书。
乌漆嘛黑的,布满印迹。
倒像那么一回事。
就是不知道是人血,还是狗血了。
“本长史知道了。既然今日有人伸冤,正好,择日不如撞日,本官也要为人伸个冤。穆之,命人去狱中,将袁成、严明带来。”
“对了,再去把桓将军请来。”
谢混吩咐完,便好整以暇地坐在堂下椅子上,静候刘穆之带人来。
袁崧拧紧眉头,有些看不懂他要干什么,但又不敢追问,只能耐心等待。
至于请愿的十余人,谢混没叫他们起来,只好继续跪着...
一刻钟后。
带着镣铐的袁成、严明先到,桓宝也随后赶来。
一时间,谢混在堂中独面将近二十人。
颇有舌战群儒的意思。
“谢长史,人都到了,您看?”袁崧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劲,小心询问。
谢混站起身来,弹了弹身上不存在的灰尘,慢条斯理道:“今日有人为袁成、严明二人伸冤,甚至还请来万民书,本长史甚是惊讶。”
“袁太守、桓将军,你们可知为何?”
袁崧、桓宝相互眼神交流一下,接着齐齐摇头:“我等不知,还请谢长史明示。”
“只因,这二人乃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
此话一出,满堂皆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