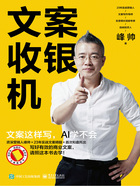
第3章 怎么通过“意会式学习”,打通文案写作的“任督二脉”?
这一章的标题看起来有点玄乎:我们经常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既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还怎么讲呢?
还是要先跟你讲一个我的亲身体验。
我因为职业的原因,从20多年前开始,有两件事是几乎每天必须做的:一件是不断地想各种广告创意,另一件就是写各种文案。有时候我加班加点想创意、写文案,或者一帮人坐在一起开创意会,但非常痛苦的是,无论如何这个创意就是想不出来,文案也是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总也写不出一个让自己满意、让别人也满意的文案。这时候会出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或者上厕所的时候,或者走路、坐车的时候,创意和文案会突然自己冒出来。请注意,我用了“突然”这个词,因为就好像创意和文案自己从脑袋里涌出来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第2章里,我跟你分享了如何通过“树标杆”来激发出体内的写作潜能,也就是要从文案的细节表现力、文案的写作技巧和特点、文案的布局和结构设计能力,以及文案的灵动性与真实性这四个层面,对你的标杆进行“精气神”的模仿。但是我在对标杆进行学习和模仿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逐字逐句地去推敲分析他们的文字,而是通过一种“意会”的方式去学习的,并且这种学习的效果非常显著。
但是我们很多人在进行文案写作训练的时候,常常会陷入三个误区,而能规避这三个误区的,是三个正确且有效的训练方法。
第一个误区:抄写文案。
你可能看到过,现在很多人在学习文案写作的过程中,会大量地抄写各种文案范本。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千万不要去抄写文案,因为抄写文案跟上学时抄写生字大不一样。在抄写生字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在“字”上面,所以你抄一遍就会加深一遍印象,抄两遍就会加深两遍印象,最后这个字你就会写了,这没有任何问题。你在抄写文案的时候,注意力反而不应该在字上,而应该在“文案”上,可是你在抄写文案的时候,注意力恰恰会被牵引到“字”上。我所认识或者所知道的那些文案高手,没有一个是通过“抄写文案”抄出来的,这甚至根本不能成为文案写作训练的手段之一,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傻练”,所以你千万不要这么做。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有效做法:心领神会,把范本刻在心里。
这个取代抄写文案的方法,我称为“心到”,也就是你要把你所欣赏的那个范本,不断地读,直到烂熟于心。我之前说过,对于标杆的文字,一定要通读,通读正是为了全面了解和感受标杆的那些优秀文字。而熟读,则是要把标杆的那些好文字深深地刻在心里。
比如,我早年对于李欣频的很多文案,都熟读到几乎能背诵的地步;钱锺书的《围城》《写在人生边上》这样的小说和散文,我也都读过无数遍,他的很多比喻句我都能背诵;冯唐有一本杂文集叫《活着活着就老了》,里面的很多文章我也都读过十几遍,很多文章的结构和内容我甚至能复述出来;当然还有李敖,我不但通读过他的《李敖大全集》,很多文章我还读过几十遍,甚至还把他所有的文章按照写作时间顺序重新排列了一遍,然后去感受他几十年写作风格的变化。
我就是这样用“心到”的方法,一遍一遍地熟读那些我眼中的范本,学习我的标杆。古人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当你在熟读范本的时候,你的心已经走进了那个范本。根据我多年的实践经验,这种潜移默化的效果要比抄写文案的效果好得多。
第二个误区:拆解技术点。
你可能也看到过,很多人喜欢拿着一个文案范本,反复拆解它的撰写技术,比如它是怎么起头的、怎么转折的、怎么举例的,然后又是怎么总结的,最后又是怎么下一个消费指令的。事实上,这种方法也非常不可取,因为拆解其实就是在寻找一种“确定性”,也就是那篇文案发生效果的一个“确定的临界点”。但是这个“确定的临界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最起码是飘忽不定的。这就好比我们知道每天都有黎明,都是从天黑开始,然后慢慢地到了黎明,最后天亮了,但是如果你非要确定黎明是几点几分到来的,显然无法确定。一盆花,你把种子埋在土壤里,它总会发芽、开花,但是如果你非要确定这盆花到底会在哪一天具体开放,显然也无法确定。真实的情况是,黎明会慢慢到来,花儿会慢慢开放,只是你察觉不到。所以,千万不要过度地拆解一篇文案。
当你学习范本的时候,其实更多要像小时候学骑自行车那样,你并不是靠拆解动作学会骑车的,而是通过不断刻意练习,练到一定程度以后,自然而然学会骑车的,那一刻仿佛任督二脉“突然”被打通了,“突然”你就学会了,这才是真正的“意会式学习”。
而写文案也一样,你把一篇文案的起承转合拆解得再仔细,你最后学到的也只是片面和僵化的技术,而不会产生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也不会真正达到融会贯通。
第二个有效做法:把自己替换成你的标杆。
这个取代技术拆解的做法,我称为“意到”,也就是你要把自己替换成你的标杆,当你在熟读那些范本的时候,你要想象自己就是那个作者,“我就是李敖!”“我就是钱锺书!”“我就是×××!”。总之,要彻底地转换成他的身份、他的立场、他的视角、他的观点、他的语言习惯……可以说,这就是一种“文字冥想”:你闭起眼睛来,假想你的标杆已经被你替换掉了,假想这篇文字就是你自己写的。
总而言之,你在熟读了范本的同时,要让你自己最大限度地“变成”作者,而不是简单地去模仿和拆解。不要停留在那个肤浅的技术层面,而要深入标杆的内心世界,这就叫“意到”。
第三个误区:纠结于遣词造句。
这也是很多人学习文案写作最容易犯的毛病之一,比如纠结这个名词要这样用、那个动词要那样用。我的文案也经常会被一些学员拿来做分析:“峰帅的这个动词用得真好!”“那个句子写得真传神!”“这个比喻用得太绝了!”当然,如果你把我的某一篇文案当成一个范本去学习,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不赞成对我的文案做过多的分析,因为你无论是写短文案还是长文案,一旦纠结于微观的一词一句,你的双眼就会被蒙蔽,你就会陷入“咬文嚼字”的状态中,无法在文案的大殿中自由徜徉。
第三个有效做法:感受作者的那种“真实呼吸”。
这个取代纠结词句的方法,我称为“场景到”。既然你现在已经把自己替换成你的标杆,你已经进入他的角色,有了他的身份、他的观点、他的视角和他的语言习惯,那么这时候你还应当进入他写这篇文章时的那种场景和语境,也就是他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目的而写的。所以紧跟着“意到”而来的,是你的脑海中一定要形成一种画面感、一种场景感、一种呼吸感、一种触摸感,真真正正地用你的意念去体会那篇文章当中所写到的场景和感受。只有这样,你才会迅速地把自己身上那种“真实的表达能力”给调动出来。
所以,我们在训练文案写作时,很多时候往往并不是在写,而是在想、在体会、在感受那种原先感受不到的“真实”。
我的“意会式”操练
举个例子。
我的四大标杆之一冯唐,在2007年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大片王朔》,写的是他对王朔和王朔文字的评价。现在看那个时候的冯唐,他的文字其实还有一些做作,不像现在已经趋于平淡了。但即便如此,他那时候文章的个性化风格已经形成了,尤其是“金字塔结构”这一点,识别度非常高。
《大片王朔》这篇文章不长,你在网上可以查到,总共大概也就一千多个字,却是我用心读过很多遍的冯唐文章之一,这属于典型的“心到”。而我在读他这些我比较喜欢的文章时,常常会想象我自己就是冯唐,我会尽可能地去体会他在这篇文章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写,为什么是这样的视角。当我这样把自己“替换”成冯唐以后,我就会进入“意到”,然后我会闭上眼睛去想:假如我不是冯唐,我还是峰帅,现在让我来写这篇文章,我会怎么写?如果不写这篇文章,让我写一篇类似的文章,我又会怎么写?
很巧的是,同样在2007年那一年,冯唐出版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北京,北京》。那时候有一本叫《TimeOut上海》的杂志向我约稿,约我给冯唐的这本新书写一篇书评。于是我就花了一个小时,飞快地写了一篇短小精悍的书评,题目叫《磁性文字》,全文是这样的。
磁性文字
刚开始工作那会儿,学习广告创意,总监说,一切的艺术、一切的创意,起步于抄,先盲目地抄,然后有选择地抄,然后懂得创造,最后懂得创造得好。我曾经设想,文字也是艺术,也需要创意,大抵也该遵循这个流程吧?
读冯唐的文字,设想得到验证。初读,感觉贾宝玉初见林妹妹似的,底蕴厚厚的,气质痞痞的,姿态雅雅的,面善。四处对照,在当代人里没找到明显的师承。后来发现,冯唐自己捅破过窗户纸:“我第一次阅读亨利·米勒比我第一次解剖大脑标本,对我更重要。……那时,我开始修炼我的文字。”读过《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读过《万物生长》,再读《北京,北京》,断定他终于过了涩涩的模仿期,自行创造,成果显著。
同亨利·米勒一样,《北京,北京》琐碎、断裂、自我,有一种难以归类的巨大力度和磁性,直接把我吸附过去。
琐碎。作家笔下无小事,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得不好,《儒林外史》那么重的大题材,给中国古人处理起来一样糟糕;写得好,逛大街,穿小鞋,吃蛋炒饭,看少妇胳膊,写来一样勾魂摄魄,绕梁千日。冯唐在《北京,北京》里,喝大酒,睡女人,坐夏利,琐碎更细微,但顺着读过去,生活立刻就树在面前了。
断裂。常常觉得,中国人的文字里,最好的小说家是司马光他们,把一部历史写得如同小说,莫名其妙开始,莫名其妙结束。像冯唐说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你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没头没脑,有的只是快感。寻丝觅迹,这种快感除了来自语言,还来自意象的断裂。《北京,北京》断裂,断裂的间隙处全是功夫,像真品景泰蓝的冰裂纹,造不来假。
自我。好多用文字永垂不朽的,不是因为开头拿自己说事儿,就是死前拿自己说事儿,比如海明威,比如卢梭,比如卡萨诺瓦。想想,写字的人,自己就是苍生,写自己就是写永恒。想象力再好,深不过经历;世事再洞达,明白不过自己。冯唐似乎深明此道,所以写到《北京,北京》,还往这路上靠,只不过他跟他的老师亨利·米勒,都是年近而立看山非山看水非水时,才拿自己说事儿,好处是过去有写头,前面还有得写。
冯唐说,《北京,北京》将是他最后一部基于自己经历的长篇小说,此后,假如他学会运用想象、胡编故事、制造高潮、提炼主题种种世俗的写作技巧,他就不做金领,就没有理由不去专职写作了。据说专职写作的人,大多守不住,写着写着就油了。琐碎、断裂、自我之后的冯唐,不知道会不会写油了,写出不再让我热血沸腾的文字,读着,让人叹一句:“冯唐易老!”
(2007年12月发表于《TimeOut上海》杂志,署名“万谷”)
和冯唐自己的那篇《大片王朔》对比阅读一下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结构上、在风格上,还是在措辞上,我这篇书评都带有很明显的“冯唐味儿”,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刻意地模仿他,而是在那个阶段的那个时刻,我已经完全把自己“替换”成了冯唐。假如你现在让我再来写这篇书评,我一定不会像这样去写了,但是正因为当时的我在经历这样一个“心到、意到、场景到”的阶段,正因为我在不断地用这种“意会式”的方法去学习,我才真正学到了我的标杆的文字功夫精髓。我用这样的学习方法打通了文案写作的“任督二脉”,然后才逐步形成了属于我自己的风格和方法。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一章最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当我们苦思冥想一个创意的时候,往往老半天都想不出来,创意却在无意之中突然就冒出来了?为什么当我们绞尽脑汁写文案的时候,经常很久都写不出来,突然之间又文思泉涌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脑海早已刻上了某种意识和某种意念,我们其实一直带着这种意识和意念在思考,这时候无论我们在吃饭、在撸串还是在走路,我们的脑子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只不过是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思考,所以才会在“突然之间”水到渠成。这跟我所说的突然学会了骑车、突然黎明到来了、突然花儿盛开了,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体现了很关键的两点,对于我们的文案写作训练非常重要。
第一,你一定要始终保持“有意识”。
也就是说你要充分地意识到你这篇文案是写给谁看的,你要告诉他们什么内容,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只有你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合适。总之,在你的心里、脑子里,一定要带上这些强烈的意识。只有当你带上了这些意识,你的所有思考、所有想法才不会跑火车,才不会是茫然的。
第二,在带上了这些意识以后,你要不断地写、写、写。
每一次想和写,都是我们在一个特定的视角和场景下“游泳”。所以我们学习文案写作,应当用这样的方法不断地展开操练。
这一章跟你分享的内容和方法,乍一看好像有点玄乎,事实上它带给你的效果,会比你漫无头绪地去抄写文案、拆解文案快得多,也好得多,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训练方法之一。希望你认真消化以后,也能在实战中认真地操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