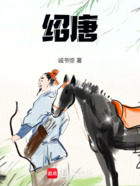
第92章 册某为帝(一)
洪武一载,十月一日。
起了个大早的李亨在郭曦的服侍下换上繁重的衮冕——一种皇帝最常用的礼服,能够应用的场景包括但不限于祭祀社稷、上告宗庙、遣将出征、天子亲征、登基即位、娶妻成亲……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衮冕应该是由下述几个部分组成:
装有黄金饰物的、专用的冠冕,冕板前后各垂十二条由白珠串成的旒,左右两侧悬挂玉制的充耳,中间插有玉簪,与发髻固定在一起;
上衣宽身大袖,黑色,上绣“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八章;
下裳是红色的多褶大裙,上绣“藻、粉米、黼、黻”四章。
以及最基础的十二章纹,日、月各一分列于左右臂之上,星辰绣于后背,龙织成于袖端、领缘,自龙、山以下各纹饰,每一章列一行,每行又十二个。
李亨的这身各种章纹倒是齐全,但其余用来彰显身份的贵重的装饰物,则是统统换成相较之下朴素一点的东西。
这衮冕李亨也就在亲征之时曾经穿过一次,如今再次套在身上,是为了迎接从成都那被基哥派过来搞册封的队伍。
只要完成了这个流程,往后就无人可以在正统性这方面指摘他李亨——虽然现在也没人敢就是了。
为了皇帝的册封大典,整个回乐在清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等到李亨整装完毕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布置基本上已经完成。
想想这还是李亨专门一再嘱托“一切从简”的结果,天知道那些喜好铺张牌面的皇帝一次大典要提前准备几天,又要消耗多少人力物力。
这之后,就是将昨日就行至城外住了一夜的册使队伍迎进城内,为首的当然是基哥钦命的三位宰执,其中韦见素居中,房琯和崔圆一左一右拱卫着他。
其实从这个阵型就能发现三人此时的地位高低:
韦见素原是侍中、兵部尚书,到达蜀郡后又加金紫光禄大夫,进封豳国公,是三人当中资历最深地位也最高的——要知道,在三省六部制极为重要的唐朝,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侍中可是被称为左相的存在,只比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右相)差了一筹而已。
崔圆本是剑南节度副大使,等到杨国忠死后,光速效忠基哥的他火速升任节度使,甚至直接得了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官衔,以节度使之身拜相。
按理说,朔方节度郭子仪和河东节度李光弼应该也会以这种方式拜相,因为在唐朝为官本就是需要文武双全的,也就是出可为将、入可为相。
不过李亨在这件事里明显有着其他的考虑在,而郭子仪和李光弼对此也不甚在意就是了。
接着剩下的房琯自然不必多说,他在叛乱前只是个小小的刑部侍郎,虽然因追驾之功而成功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预政事,不过从本职官品就能看出来,这时的房琯还只能陪在末位。
事实上,房琯真正发迹,也是因为肃宗的看重。
三人联袂而行,直到在御前班直的带领下见到十分庄重的祭坛,这才停下又细细地整理了一遍衣着,这才一步步的拾阶而上。
这祭坛通体洁白,整体呈圆形,一共有四个阶层,在八个不同的方位上都布有一级级的台阶,无论从哪个方位上去,都能抵达最后的目的地——也就是最顶端的、目测离地有七八米的圆形高台。
此时此刻,那高台上已经满布着各种仪仗和各色人影,或是因为空间太小的缘故,倒是显得过分拥挤了一些。
不过这祭坛本就是当初李亨登基之时临时建起来的,现在能够拿来废物利用一番,不用再有多余的支出,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韦见素带着两人迈着缓慢但坚定的步伐走到皇帝面前,先是拜见了皇帝,然后跟着皇帝一起祭天,完成了一系列繁冗的礼节步骤之后,才从自己的袖袍里郑重地掏出两份诏书。
为了保证其不损坏或者遗失,韦见素一向是将其随身携带的。
他先将其中一份交给崔圆拿着,然后自己摊开一份大声念道:
“敕:帝王受命,必膺图箓,上叶天道,下顺人心,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取,是故我国家之有区夏也。”
“……”
“……”
“昔尧厌倦勤,尚以禅舜,高居汾阳,况我元子。某睿哲聪明,恪慎克孝,才备文武,量吞海岳,付之神器,不亦宜然!今宗社未安,国家多难,其英勇雄毅,总戎专征,代朕忧勤,斯为克荷。
“宜即皇帝位。”
“仍令所司择日。宰相持节,往宣朕命。其诸礼仪,皆准故事;有如神祗简册申令须及者,朕称诰焉;衣冠表疏礼数须及者,朕称太上皇焉。”
“且天下兵权,制在中夏,朕处巴蜀,卒应则难。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皇帝处分讫,仍量事奏报。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诰制所行,须相知悉。”
“皇帝未至长安已来,其有与此便近;去皇帝路远,奏报难通之处,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仍令所司奏报皇帝。”
“待克复上京已后,朕将凝神静虑,偃息大庭,纵姑射之人,绍鼎湖之事。”
“……”
“……”
“朕之传位,有异虞典,不改旧物,其命维新,奉禋祀于祖宗,继雍熙于宇宙。布告亿兆,咸使闻知。”
随着最后一个“知”字重重落下,韦见素心中也仿佛被大锤敲击。
他当然没有提前看过这篇由贾至所拟的、在后世被称为《明皇令肃宗即位诏》的诏令。
只是以他的水平,即使只通读过一遍,也已经完全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无非就是成都的那位已经成了上皇的不甘心于放权,于是在即位诏书中动了手脚。
看似变诏为诰,实则依旧保留了自己任命官员的权力;
更别说那句“诰制所行,须相知悉”,明面上看是要互通有无的意思,但实际上不就是把之前一个皇帝的权力分润给了两个,一个天子变成了两个天子吗?
这哪里是传位?
韦见素在心中打了个寒颤,经历过诸多事件,以他这个年纪,也只想要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谁愿意再卷入到斗争——尤其是两个皇帝的斗争——当中去?
神仙打架,可千万别危及到老朽这个传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