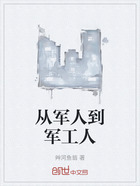
第14章 上山当知青
我下乡的老家永川县,是一个山清水秀、富饶美丽的好地方。它位于长江上游北岸、重庆西部,距重庆城区63公里,于唐代大历11年(公元776年)置县,因城区三河汇碧形如篆文的“永”字得名,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
永川西南部的来苏区,区委区府驻地来苏乡,建场于宋代,历为永川县文化重镇、CQ市中心镇、全国重点镇。来苏的蚕桑、仔猪、再生稻被誉为农业“三绝”,全国闻名。
“来苏”这一名字的由来,据说与宋代那位才情横溢、名满天下的大文豪苏东坡有着不解之缘。传闻,他曾到此游历,故而此地得名。
在距离来苏场口约1公里处,向左转便能望见太平山。这座山的东北面,矗立着上下相叠的巨大圆石,其地势颇为奇特,三面临着悬崖,一面紧靠着绝壁,此景被称作梳妆台,在永邑之地,堪称奇特又著名的景观。
关于这梳妆台的由来,还有一段美妙的传说。据说,古时曾有六块巨石从峨眉仙山飞跃而来,落至来苏。其中一块石头落入观音堂,化作了蚌壳石;另有两块巨石停在了太平山东端,它们直立于高崖边缘,看似摇摇欲坠,却始终稳稳地悬于那里,让人顿感奇妙,因而得名活石头。又听闻,曾有仙女在这活石上梳妆打扮,所以人们便以梳妆台来称呼此处。其余的石头,有的形状如同几凳,还有两块分别名为金柜和银柜,它们紧紧依偎在梳妆台旁。
北宋时期,大文豪、大居士苏东坡听闻此处奇景,慕名前来游历一番。清乾隆年间的《永川县志》也曾记载:“永川有镇,名曰‘来苏’,东坡曾游历至此,因名”。来苏的文化脉络源远流长,直至今日,依旧处处彰显着对东坡居士的敬重与缅怀。在场镇之中,修建了东坡广场、东坡大道、东坡小区以及东坡大酒楼;机关里开办了东坡讲堂;学校内还树立起了东坡雕像,“东坡遗风、诵读乐园”的氛围愈发浓厚。
说来也巧,我下乡插队的老家,竟然与我自幼便十分敬仰的苏轼有着这样的关联,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每每念及,心中都满是亲切与自豪。
来苏之地,地势平坦开阔,河曲纵横交错,自古以来就享有“来苏坝子”的美称。来苏区下辖的文峰公社,则位于来苏坝子边沿的黄瓜山上。
黄瓜山平均海拔高度600米,森林覆盖率约40%,自然环境优美,风光旖旎,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年平均气温较城区低4—6℃,夏季凉爽舒适。
刘禹锡的《陋室铭》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黄瓜山上就有永川县规模最大的佛教圣地大佛寺,香火旺盛,僧尼每天都要做拜佛诵经的朝募课,每月初一、十五亦举行拜佛诵经的活动,每年还要举办几次庙会,前来进香的善男信女熙来攘往,游人络绎不绝。
山上还有一个石油钻探区队,有一条从永川到泸州的公路贯穿整个山脉。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的基本单元,还承担着基层政权的职责,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公社之中设有党委,在各项事务里,公社党官员发挥着关键的引领作用,而社长等行政领导人员,一般也都是党委委员。
公社之下又设有若干生产大队,在大队的事务决策方面,党支部书记往往有着重要的话语权。生产大队再往下,便是生产小队。生产小队这一级别,由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以及妇女队长等共同组成队委会,通过集体的方式来领导小队的各项事务。
我下乡当知青的地方是文峰公社八角大队五小队,那里主要以粮食种植作为主要产业,副业方面,则有一个由大队开办的采石场,还有一个茶场,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黄瓜山林木茂密,石料丰富,石匠手艺好,青色条石在当地是很有名的。八角大队采石场位于永泸公路旁边的一个山凹,生意很好,每天来拉石头的汽车要排队。
黄瓜山出产的茶叶是针形茶,属于绿茶类,泡一壶清香扑鼻,喝一口泌人心脾。八角大队的茶场位于山脊一边的一片茶山,茶树顺坡环山栽植,一梯一梯层层叠叠,但规模不是很大,产量有限。
与平坝上的公社比起来,文峰公社因为位于山区,在当地算是比较贫穷的。生产队的农作物交了公粮后,全年人均口粮大约几百斤谷子和几十斤小麦,还有红苕、包谷、豆子等等少量杂粮,数量上有点紧张。山上的土地以种植粮食为主,以及一些的油菜、蔬菜等。当地的农民,除了春节、中秋等几个传统节日,平时很少见他们吃肉。
当地农村不通电,也没有自来水,公共文化设施也少,物质生活贫乏,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农民的日子艰苦平淡,但他们豁达乐观、他们也直率粗鲁,他们承担着沉重的劳动还心态平和,这使我印象深刻。
我们乘坐的火车于中午时分到达永川火车站,我与随车送我下乡的母亲下了车。火车头很快长鸣一声,又喘着粗气,拉着更多的知青驰向了更远的远方。
我们出了站台,在站前广场换乘客车。陈旧的大客车缓缓驰出永川县城南门,沿着一条蜿蜒盘旋的石子公路,一路颠簸上了黄瓜山。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呆呆地望着车窗外掠过的田园风光。远处层峦叠嶂,黛色的山形起伏不定,像是一个姑娘的侧影,端庄而妩媚。公路两旁不时出现一片片树林,一栋栋房舍,有小溪淙淙地流淌着清澈的溪水。路旁的田地里,一些头戴草帽的农民在忙碌劳作。
大约下午2点多钟,我们在黄瓜山上的文峰公社下了客车,一行人来到离车站不远的公社所在的院子。院子不大,中间是一栋面对大门的两层小楼,两边各有一排平房。
公社干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办理了简单的手续后,安排我们在公社的食堂吃了午饭:大碗菜、大盆菜汤和米饭。其间在公社大院碰到一个永川县城下乡的知青,他听公社干部说我是刚下乡的重庆知青,便笑容可掬地过来打招呼。简单交谈了几句,他就热情邀请我参加知青的活动。原来他在组织公社蓝球队,我满口答应。他从口袋里掏出纸笔记下了我的名字,掉头进了公社院内的广播室。我们一行人在公社干部的陪同下,来到离公社不远的公交车站,乘客车前往生产队。
八角生产大队第五生产小队地处黄瓜山上一片平坦的山脊,永川县城至文峰公社的公路从山脊中间穿过,公路两边树林茂盛,周围是一片接一片的水田。八角大队的书记已经接到公社干部的通知,带领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在车站等着我们。
站在八角大队大队部瓦房前面的三合土坝子上远眺:永沪公路的左侧半山腰的树林深处,有一个在建的小水库,由大队各生产队抽调的民工组成常年施工队施工。民工们采取评工记分的方式,各自回队参加当年分配。从小水库再往下走,到山脚便是永川卫星湖水库。卫星湖水库长约8公里,面积约1500亩,有多个自然形成的半岛和全岛,湖弯交错,碧波荡漾,景致优美。水库东面靠山的一边有一个军工科研单位;西面是永川师范专科学校校区(后更名为重庆文理学院)。黄瓜山左面山外平坝属于永川县石脚区。
公路的右侧植被丰富,远处的拐弯处有一条岔马路,那里的葱绿山梁上有一个大队开办的采石场塘口,一片青山裸露出黄色的泥土,特别的刺眼,活像大自然身上的一块伤疤,有点大煞风景。岔马路更远的那一头有几间草屋,过了草屋,顺山势修有陡峭的石阶,通往山脚一个名叫“踏蹄沟煤矿”的小煤窑,煤质相当不错。黄瓜山右面及山外平坝属于永川县来苏区。
我们在大队部稍坐片刻,又是一番寒喧,然后登记填表。该办的事很快就搞定了。喝了几口茶,说了几句客套话,当地农村的干部们便带领我们沿一条乡间石板路,前往第五生产队。直接来到生产队为我安排的住房。
那是一个掩映在一片翠竹间的普通农家院子(在当地有竹丛的地方必有院落或住家),院子面对大约100米左右是生产队的保管室,中间只隔着几块水田。保管室前面有一块三合土大坝子,生产队每年秋天收了谷子在坝子上晒干后,就存放在坝子边上的几排草房里。作为粮仓的草房的对面,也有一排草房,其间的几间门上有把锁,存放化肥、农药、犁耙等生产资料;外面有一间放有几张桌子、柜子和不少的长条木凳,有点类似于办公室,平时开会也在这里(干部开会学习在房子里,社员大会则在坝子上开),这是生产队的行政中心。
农家院子的背后是一个低缓的小山坡,山坡上绿油油的一片,长满低矮的桐油树。一条石板路边有一个小堰塘,堰塘的水面反射着明晃晃的太阳光,据说平时洗衣服就在小堰塘里。一口水井离院子不远,挑水很近。
整个院子呈品字型结构,在中间又插了两间小屋,原住有四家人。左边第一家的主人是大队贫协主席,一如他的职务,家庭十分贫穷。紧挨着贫协主席的是生产队的会计一家,会计是个30多岁的退伍军人,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这家人两口子生反了相,男会计长相秀气,老实厚道,说话轻言细语,做事细细摸摸,象个女人家。他的老婆却生得宽皮大脸,像个男人一样热情爽快,说话喉咙粗,耿直得略显粗鲁。
右边的两户人家,第一家住着一个50年代下乡的老知青,因家庭出身不好,回城无望,所以在农村安了家,有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据说中年老知青练过武术,学过中医,是个农忙时下地干活,农闲时背着药箱行医的郎中。另一家的男主人出身贫农,是个蔫不啦叽,老实巴交的农民,身材矮小,心眼也小,是个典型的“耙耳朵”(怕老婆)。这家的女主人是个干部(大队的支部委员),身材高大,性格有点偏执。两口子膝下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读小学,一个女孩只有两三岁。院子中间的两间低矮小屋,住的是一个下乡五、六年的永川知青,中等身材,面相成熟,已与当地农民结了婚,但老婆住在娘家,有时来住一段时间,没有小孩。兴许是生活的重压或希望的渺茫,这个知青显得孤独忧郁,与周围团转的人显得格格不入。
分给我的房子居于院子横排的正中间,紧邻会计家,是只有一扇窗户的破旧瓦房,大约30余平方米,原为生产队的柴房,我既作卧室也是厨房。进门左面靠墙是一个土灶,紧挨着是一个水缸。灶台的后面用来堆放煤炭、柴禾和农具。屋里的物品大都是旧的,只有锅、瓢、碗、筷、煤油灯、水桶等少许生活用品和锄头、镰刀、扁担、箩筐等常用农具是新买的。墙角的粪桶白天是农具、夜间用来解小便。右面留的空间稍大一些,只有几件简陋的木制旧家具,一张木床旁边有个柜子,柜子的两扇门坏了一扇。唯一的一张八仙桌,既当饭桌也是书桌。桌子旁边有一张条凳和两张木凳,平时吃饭和读书都坐木凳,没有带靠背的椅子。知青屋不少地方的墙壁上石灰已经脱落,屋顶被烟熏得黢黑,屋子灰暗得宛如我的不确定的未来。
初次走进这间略显空旷而又阴暗潮湿的房间,放下带来的行李,母亲一言不发为我铺床,挂蚊帐。我把衣服棉被等收进柜子里,但书籍、本子等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屋里没有书架,只好将带来的书和笔记本,一本叠一本地放在一个人造革的提包里,放在一个米柜上。我不免感到有种酸楚,一片凄凉涌上心头。
我不断调整心态,告诫自己“不要在乎条件的艰苦”。心比天高的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我会走的”,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使自己心态平和的自我安慰。
当时农村的很多地方都建立了有线广播系统。公社大院有一间专门的播音室,安装了扩音器和高音喇叭,各个生产队的有线广播传输线也基本上进到大多数住户。我的屋子里也装有广播喇叭,每天早晚定时转播半个小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其余半个小时由公社播音员或宣读上级文件、或宣传政策、或播放样板戏等等。凡是公社有生产、学习、开会等安排也是由广播进行通知。在无报纸可看,更没有普及电视的广大农村,广播作为一种传统传播载体,在当时发挥了其它媒体难以企及的作用和优势。
我到的当天傍晚,就在公社的定时广播中听到了我的名字,内容是通知我和另外几个我还不认识的知青,一周后到公社集合打蓝球。
黄瓜山位于四川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上世纪50年代,川东石油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在黄瓜山上开采有若干天燃气井(我们大队地界内也有一个天燃气管理站)。几天后我去了,我们知青蓝球队训练了一天,与川东石油管理站职工蓝球队,在石油分公司蓝球场进行了几场友谊比赛。
夏天的夕阳映照着一片绿水青山,充耳所闻是鸡鸣犬吠与飞鸟的婉转啼鸣。放眼远望,缓缓起伏的丘陵间分布着零零星星的幢幢房舍,四周升起一阵阵袅袅炊烟。三五农民正围坐在自家房前绿树下的小桌吃晚饭,生活简单而又恬静。
在生产民队会计家里,农村干部们陪我们吃了晚饭,便分别回了公社和大队,母亲乘客车到永川县城的二姨家。我收拾了一下房子,天就黑了。暮色笼罩的山村里,妇女们带着针线活儿互相串门聊天,话题多是谁家结了媳妇、生了孩子;汉子们则聚在空地上抽烟闲侃,谈论今年的庄稼收成,或相互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点滴的生活波澜就是他们话题的全部乐趣。
这里的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纯朴勤劳、热情好客,怡然自乐的古风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