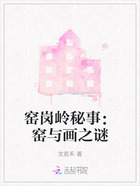
第4章 窑火虽尽怨难消,情缘难续梦更遥
公元1096年农历八月,窑岗岭的秋夜早已褪去了夏日粘稠的暑气,三座桂州窑盘踞在江畔,窑顶腾起的青烟与星河相接。十二岁的秦秋芸踮脚去摘窑场旁盛开的桂花,素色裙裾扫过满地碎瓷,发出细碎的呜咽。
“当心釉毒!“少年清朗的嗓音惊得她踉跄后退,绣鞋踩进松软的窑泥。蒋至谦从窑口探出头来,鼻尖沾着草木灰,手里握着半截测温用的观火镜。月光淌过他束发的青布巾,在深褐色的瞳孔里凝成两盏跳动的窑火。
“你来做什么?“秋芸攥紧衣角略带羞涩地问道,露水打湿的刘海贴在她的额前,她下意识地理了理。
少年并不回答,却将观火镜横在眼前,镜片折射出漫天星子:“你看,碎瓷里的星星比天上还多。”他指尖抚过地上的青釉残片,轻叹一声,“可惜了,再难烧出如冰似玉的青瓷了。“
秋芸刚要伸手捡起那些青瓷残片,远处忽然传来瓷器碎裂的巨响。秦家老爷的暴喝混着蒋父的咳嗽声撕破夜色,两盏灯笼在窑场东头剧烈晃动,光影中飞溅的瓷片像极了除夕夜的烟火。
“又是为那樽碎了的冰青釉。“至谦拉着秋芸躲进窑洞,温热的手掌捂住她发凉的耳垂。去年冬至,官家订制的青釉瓷尊在开窑时炸裂,秦家老爷就怀疑是窑工蒋初平偷换了釉方。
窑洞里的热浪裹着松脂香,秋芸数着洞壁上交错的火痕,那些深浅不一的灼痕恰似母亲临终前手背的脉络。至谦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层层剥开是块桂花酥,糖屑间粘着张泛黄的《桂窑秘录》残页。
“等我能掌窑了,定要复烧月白凝脂釉,到时给你烧一个玉壶春瓶,每天插不同的花。“少年擦拭了一下页角焦痕,那里似乎藏着桂江山水与釉方密语,“我YA(爹)说桂州窑的秘釉,非得用桂江源头之水调釉,在窑神庙祭过窑火才能成器。“
秋芸含着半块糖,看月光在观火镜中碎成粼粼的江水。她忽然希望这场争吵永远不要停歇,好让窑洞里的光阴凝成釉料,将此刻封存在永恒的窑变中。
然而随着景德镇瓷器的兴起,桂州窑出的陶瓷行市大不如从前,秦家的陶罐青瓷经营日趋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老窑工在一次建窑时不慎从上面摔下,后脑勺撞到一块青石板,当场人就没了。秦家老爷虽有一儿一女,无奈儿子自小骄纵,难成大器。眼见窑场难以维系,他唯愿女儿找个家境殷实的人家,多少能帮衬重振起家业。
秋芸又何尝不明白父亲的心思,但她早已心有所属,奈何一闺中女子如何明说,但凡有人上门说媒,只是以各种缘由一一婉拒。
蒋至谦虽自小跟着父亲住在秦家,秦家老爷也知其聪敏好学,只可惜出身低微,实在门不当户不对,蒋初平出事后,秦家老爷补贴了他些生活银两便将其辞退了。“多情自古伤离别”。至谦未跟秋芸告别就匆匆带着母亲走了,走得不舍却又无可奈何。等待他的是太多的未知,他不能让秋芸跟着自己受苦。几天后,秋芸才得知至谦已经走了。纵使她苦苦哀求,父亲也没告知她至谦的去处,只是把至谦手绘的一幅山水画交给了她。画中正是他们曾经一起畅想过的生活,山水环绕而居,制瓷烧窑为生,平淡富足,生儿育女,代代相传。可是至谦悄无声息地走了,把她的心也带走了。她想把画撕碎,却又不舍得,紧紧地拽在手里。渐渐地,泪眼模糊了她的双眼,她开始抽泣,然后撕心裂肺地哭嚎起来……
没过几年,秋芸在父亲的安排下嫁为人妇。蒋至谦带着被辞退的银两一路往东走,在藤州一个窑场找到了活路。他是在窑场长大的,什么“土、火、柴、窑的关系”,“配制陶土、手工制坯、素烧成型、配釉上釉、复合窑烧”的流程,以及釉方的比例,这些他从小耳濡目染。在藤州的中和窑场,他踏实肯干,勤学技艺,很快就成了窑场的大师傅。街坊邻居见小伙实诚能干,热心帮着说媒拉纤。只是他心中尚有所念之人,对说亲之事并不热心。但“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为不孝,恐母亲催促,经媒人牵线,将苍梧县多贤乡六堡一茶农家的女子娶回家中,至此在数百里之遥的藤州落地生根。
十余载春去秋来,一日,雨幕中忽然传来中和窑开闸的轰鸣,几重窑门次第洞开,蒸腾的水雾里浮动着翡翠色的光晕。蒋至谦赤着上身站在窑口,汗水沿着他的脊背滚落,在满窑青瓷的辉光中化作一股涓涓细流。他手中那支青白瓷素纹高足小碗釉质轻薄细腻,白中泛青,青中透白,积釉处略带水绿色。
“成了!“蒋至谦清亮的嗓音刺破雨帘,他捧着青白瓷碗的手在发抖。多少个日夜苦心琢磨,多少次釉方配比调整,他终于烧出这般莹润均匀的釉色。
青白瓷高足小碗的烧成让蒋至谦成了远近闻名的烧窑大师傅。消息很快传到了秦家老爷那里,让他更坚信蒋家偷了秦家的釉方和技法。气恼之下,他定下了不允许秦家子孙与蒋姓通婚的族规,还把所有蒋姓窑工都赶走了。
青白釉或许只是蒋至谦一次偶然的机缘巧合,他更渴望烧成的是那款月白凝脂釉,他始终念念不忘的是要送给秋芸一个玉壶春瓶。他知道,唯有用桂江源头之水调釉才有希望。怀着这个执念,也为了完成母亲与父亲合葬的心愿,已近暮年的他又悄悄举家回到了窑岗岭。
光阴一去又数十载,物是人非。蒋至谦重新回到窑岗岭时,秦家老爷早已故去,秋芸原本就体弱,五十出头也病逝了。
他给秋芸那份褪色的承诺,就像画里的夕阳,永远悬在触不到的远方。他穷尽了最后的十几年生命,也未能烧成秦家窑曾烧出过的冰青釉和月白釉。随着桂州窑的衰落,秦家和蒋家的后世子孙们也渐渐对烧窑失去兴趣,大都转为务农了。曾经的窑史和祖辈的往事都被时光冲淡,只有那幅画成了一代代流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