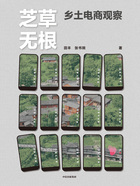
童年
丁浪小时候总觉得家里穷,从记事开始,父亲就在外面打工,其间有几年过年都没有回家,如果家里需要买东西,就得从地里面收割一些农作物,一般是应季的豆子、洋芋,只有赶场时把农作物卖得了钱,才能去购买生活必需品。丁浪来到焕河村之后才知道,原来在德江县,自己小时候不算穷的,跟焕河村的人们相比,自家条件要好很多。其实,丁浪家住得离县城并不远,属于堰塘土家族乡高家湾村丁家山组,丁是村里的大姓,其他人家有姓吴、谢、罗的。丁家人主要居住在靠近公路一侧,他家正好对着326国道,打小就能看到门口飞驰而过的大货车。在2015年沿榕高速德江段通车之后,丁家山恰好把在了高速收费站德江南站,现在过往的车辆更是络绎不绝。从丁家山开车去德江县城,大概只需要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说是离县城最近的乡镇了。丁浪出生时正好赶上贵州省政府提倡农村居民外出务工。贵州几乎任何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是人多地少,丁家山也不例外,丁浪家里只有父亲和奶奶分到了两亩多地,要养活一家六口,颇有点入不敷出的意思。眼看家里三个娃娃快到开销大的年龄,再看看村里一些出去打工赚钱的人开始翻修老房子,加上口口相传的外面的花花世界,丁浪三岁时,父亲也跟着村里人远赴广东务工,留在家里的妈妈、孩子和奶奶组成了一支生活窘困的完整版“386199部队”。
家门口是公路,丁浪小时候去附近的集镇赶场,不需要走太多的山路。不过,父亲不在家,母亲并不是很放心带着丁浪去赶场,很多时候丁浪只能羡慕地看着邻家小伙伴拿着赶场买回来的玩具和吃食。时至今日,丁浪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赶场的情景。“第一次去赶场,回忆起来,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碗粉。因为那时确实不是那么富裕,所以到现在还能记得,我妈让我去吃的那碗粉。粉摊上是支起来的大红色太阳伞,两边全是人。一排一排煮粉的灶头就摆在街边,大家就在街边坐在小凳子上低头吃,我们这边叫‘吃晌午’。我(看到后)就说饿了,然后妈妈就叫(摊主)煮了一碗粉,自己没吃,就看着我吃。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对我自己影响比较大,也比较(受)触动。有很多东西,就是现在看来(很平淡),(但)却是那个时候的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爱(的一种表达),那种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之所以能有那么清晰的记忆,大概是因为丁浪第一次去赶场的时候已经在上小学了,更小的时候妈妈怕他走丢,根本不敢带他去。丁浪还记得有一次赶场真的走丢过。那天,人特别多,矮矮瘦瘦的丁浪背了一个大大高高的背篼,背篼的边沿高出了脑袋,远远地从他身后看去,像是一个背篼在晃动着前行。他被前面的人遮住了视线,走过去走过来,碰到人后背篼又磕在头上,无奈只能顺着人流向前挪动,还得努力保护脑袋,小心翼翼地跟着妈妈。走着走着,丁浪突然发现前面的人不是妈妈,一时惊慌失措,快吓哭了。妈妈从旁边挤过来找他,显然也有些惊慌,因而见面之后不是重逢的喜悦,而是一顿臭骂。这让他对赶场有了一些心理阴影,但没有减少他对赶场的热爱。当然,丁浪也喜欢去街上(县城老街),更喜欢去外公家。大概是缺乏父爱的缘故,丁浪身上的男性气质更多来自外公的熏陶,可以说在初中之前,外公是陪伴他最多的男性亲人。外公是木匠,动手能力很强,调皮的小丁浪很快耳濡目染学会了用竹子编制各种器物。丁浪从小跟着外公去打猎,一枪打出去,一个火花喷出来,毛鸡(野鸡)掉了下来,拿回家就变成了餐桌上的美食。[1]
跟外公在一起打毛鸡的快乐,并不能缓解贫穷带给丁浪的焦虑和不满。尽管2006年起,当地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再需要交学费,但供一个孩子读书总免不了给家里增加各种支出,所以家里一直拖到丁浪八岁时才送他去上学前班。因为那时父亲外出务工赚了钱带回家来,家庭经济状况才有好转。丁浪入学后只过了一个学期,小他两岁的妹妹也在同一个班级里上课了。“我要上学的时候家里怎么就没钱?”作为被奶奶宠惯了的幺孙,丁浪有些心理不平衡。平时家里有什么吃的,奶奶都会悄悄给他吃,根本不让哥哥和妹妹看到。好在学校距离县城比较近,乡里的教育资源还是比较好的,朱家沟学校不仅有学前班、小学,还有初中,在德江县都算是比较好的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