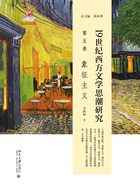
第二节 波德莱尔与颓废文学的渊源
象征主义思潮从小的圈子来看,源自与颓废派的对抗和竞争,从大的圈子来看,又是从颓废派走出来的。象征主义诗人与颓废派诗人的融合与敌对关系,让象征主义的思潮史变得扑朔迷离。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象征主义的概念进行了多次暴力性的更改,每一次更改,象征主义和颓废的关系就得到新的调整,而象征主义思潮的渊源问题就像一张被劣质的橡皮擦过的草稿,愈发模糊了。追踪象征主义思潮的起源,就要与象征主义的每一次变形对抗,寻求重造以前存在的秩序。
要完成这个任务,最好先不去区分什么是颓废,什么是象征主义。不去区分什么是颓废派,什么是象征主义者,也能避免一些麻烦。尽管在论述的过程中,本书仍旧会小心地比较它们在具体运用中产生的差异。
一、波德莱尔之前的文学颓废观
颓废( décadence)在法语词源上看,来自拉丁语词“ cadere” 。后者是“落、倒”的意思,前面加一个介词“ de” ,表示动作的趋势。合起来的意思是“垮掉、倒塌”。具体到文学艺术中,指的是旧的伟大标准的倒塌,因而含有反崇高、造作、消极、含糊不清等意思。洛曼( Sutter Laumann)曾经解释过这个词在颓废派中的意义:
一些人一开始就在颓废这个词平常的意义上,即在它原本的意义上使用它。是的,他们说,法国文学到达了它的顶点,只能下降,只能衰落。因为表达完了所有这种可以表达的,说完了所有的感情、所有人类纯朴、自然的激情,用过了所有的语句,现在只有通过寻找古怪的、意料之外的效果,寻找铿锵但无用的词语和句子,寻找所有语言都使用的外来语,法国文学才重新能让人感到震惊、愉悦和迷人。1
这段话透露颓废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它表现为不正常的、古怪的字眼。在情感上则是嗜好“纯朴、自然的激情”之外的情感。虽然颓废文学本身的宗旨并不是反传统,但是因为与正统文学清醒的距离意识,所以衍生出反传统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具有反正统的文学和艺术,都是颓废的。
对于欧洲的诗人来说,最早的颓废文学并非存在于国别文学中,而是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古罗马的诗人维吉尔( Publius Vergilius Maro) 、贺拉斯(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树立了辉煌的典范,但是之后的诗人,既缺乏前辈们的主题,又缺乏艺术能力,必然会陷入颓废之中。尼扎尔( Désiré Nisard)曾指出,罗马诗人吕坎( Marcus Annaeus Lucanus)的时代就是一个颓废的时代。当时,诗人们已经无法再使用史诗的主题,而个人的诗还未充分成长,诗人们只好破坏语言,以掩盖他们创造力的缺乏。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正好处在与吕坎的时代相似的环境中。古典主义的主题已经穷尽,尽管法国作家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有许多新的主题,但是诗人们仍旧尝试颓废的语言和风格。尼扎尔注意到两个时代的许多相似性,首先是博学与描写:“在博学之后,描写是颓废最确实的标志。描写充裕的地方,我怀疑作品的内容是单薄的,就必须用最肤浅的次要内容来填塞主题。”2这种论述提醒人们,巴纳斯派的描写,可能也是文学颓废的一个体现。尼扎尔还注意到,两个时期的文学“都有模糊的、笼统的词语”3。措辞的模糊,就像上面已经谈到过的那样,是文学颓废的重要特征。
法国浪漫主义的诗人们,与文学颓废的发展也有关系。雨果就是一位重要的颓废作家,拉斯特( Arnaud Laster)曾评价道:“雨果巨大的影子飘荡在现代文学所有的路口”4,但在有些批评家那里颓废并不是那么值得欢迎。多勒维利( J. Babbey d’Aurevilly)就是这样的批评家。他指出:“雨果先生,他并不是一位素朴的诗人,旨在创造田园诗,但他毕竟是个诗人,一位并不纯朴的诗人,但过于精巧,完全是一位颓废者,但仍然能感受到大自然,当他用人工的色彩来描绘它时,就给我们描绘了普吕梅大街的花园。”5文中的“颓废者”和吕坎的用法一样,并不是完全正面的意思。多勒维利想批评雨果的颓废。不过,多勒维利的文章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告诉人们颓废者并不是20年之后才变得重要的一个专有名词。
二、波德莱尔的颓废
波德莱尔与颓废文学的关系,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维尔哈伦曾指出:“所有当前的文学一代是从他那里走出来的,这一代狂热地学习、实践的是他,这一代描摹、模仿的是他。”6在波德莱尔身上,后来的颓废者以及象征主义者,几乎可以找到他们想要的所有理念,尽管波德莱尔并不是唯一的源头。这些理念有感应、通感、形式自由、象征和暗示手法、音乐性、综合艺术等。就这些理念来说,波德莱尔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原创者,不难发现感应说、综合艺术说、通感、象征手法,早就在雨果、瓦格纳、戈蒂耶的作品中得到了实践,更不用说爱伦·坡和德拉克洛瓦( Eugène Delacroix)给予波德莱尔慷慨的馈赠。但是波德莱尔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把之前的许多元素都卓越地融合起来,重造它们,最后成为后来诗人们的样板。巴尔曾指出波德莱尔让象征主义者们“拥有的不再是叔祖父,而是一个父亲”7。
波德莱尔对后来的颓废文学的第一个影响,是感受力。这种感受力并不是平常意义上的心灵的敏锐,而是一种对超自然世界的感知。波德莱尔生活的时代,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之前,教会和宗教观念还有很大势力。超自然的感受力有当时文化的背景。不过,浪漫主义美学家很早就给这种感受力做了准备,波德莱尔并不需要费太多的脑力。德国美学家诺瓦利斯( Novalis)曾指出:“相信人无法拥有置身他之外的能力,没有自觉超越感觉的能力,这是最古怪的偏见。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超感觉的存在。”8神学家斯威登堡( Emanuel Swedenborg)为《恶之花》的作者所敬重,他也曾宣扬能够与天堂交流的感应的能力。这些思想让波德莱尔有了远离现实生活的理由。他在书信中说:“很久以来,我说过诗人是最有理性的人,他是极聪明的人。我还说过,想象力是最科学的能力,因为只有它能理解普遍的相似性,或者理解这种神秘宗教称之为感应的东西。”9感应在斯威登堡的学说中本身就是能力,但也同时是一种境界。波德莱尔想用想象力来把握这种境界。他的想象力代替了神学家的工具。波德莱尔诗中有许多幻觉的、神秘主义的形象,它们就是这种感受力的具体化。
第二个影响表现为象征。波德莱尔的象征只有参照他的感受力才能真正理解。象征并不是意义的类比,不是另一种隐喻,它是神秘的感受力的产物。当诗人看到了一个超自然的世界,生活的本相就会清楚地显现出来,产生一种图景。这种真切的图景,就是象征。因而,在象征中,诗人可以看到世界的感应,而感应的结果,又产生具体的象征。这是象征在波德莱尔那里的第一层意思。它的第二层意思与感受力也有关系。斯威登堡表示:“大地上的任何事物,大体上宇宙内的任何事物,都有感应。”10如果人们获得卓越的感受力,就会发现神学家所说的普遍存在的感应。既然如此,诗人眼前的一景、一物,就都与更高的存在发生联系,就是那看不见的更高存在的象征。感应的世界在这种象征中露出光来。受到德拉克洛瓦的影响,波德莱尔将眼前的世界,看作是“象形文字”,其实就是象征的语言。在常人眼中,这些“象形文字”是晦涩的,缺乏意义的,但是在真正的诗人那里,它们会清晰地裸露它们的意义:
一切都是象形文字,我们知道,象征的晦涩只是相对的,即是说对于心灵的纯洁、善意、天生的判断力来说是相对的。如果诗人(我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用这个词)不是一位翻译者、一位解读员,他是什么呢? 在杰出的诗人那里,没有隐喻、比喻或者绰号不在实际的环境中发生了数学般精确的转化的,因为这些比喻、这些隐喻和绰号,来之于取之不尽的普遍相似性的井泉,它们无法取自他处。11
波德莱尔对颓废文学的第三个影响是迷醉的心理状态。因为对世界怀有一种多层的认识,进而对超自然的世界有向往之意,因而产生了对现实的厌恶和对另一个世界的迷醉。需要注意,尽管具有浓郁的宗教气息,波德莱尔的世界观又与天主教神学的世界观不同,它具有一定的异教特征。诗人曾在日记中记道:“神秘主义,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纽带。异教和基督教相互证明。”12波德莱尔并不是基督徒,他具有批评家所常说的“恶魔主义” (或撒旦主义)。艾略特认为波德莱尔“本质上是一个基督徒”,具有一种“原始的或者萌芽的”基督教精神13,这很难让人认同。波德莱尔确实对罪恶有比较清醒的意识,但是他甘愿放纵自己,他在与超越世界和正统教义的对抗中,还发展了人性的迷醉。他曾这样坦白:“非常幼稚,我感觉到我的心灵中有两个矛盾的情感:对生活的恐惧和对生活的迷醉。”14这两种迷醉似乎是一组矛盾,一个代表的是神性,一个代表的是肉欲,但是这两种迷醉却又真实地存在着。它们相互补充,又有对立,既给波德莱尔安慰,又折磨他。
第四个影响是神秘、阴郁的风格。因为向往超自然的世界,希求从自然这部象征的辞典中看出世界的真相,波德莱尔的诗作就具有了神秘的风格。这种神秘的风格表现在感应的主题上,比如他的诗《飞升》( “Élévation” )和《感应》 ( “ Correspondances” ) 。后者是人所共知的名篇,它开头两句说:“自然是一座圣殿,那里活的柱子/有时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15在《飞升》中,诗人宣称:“超然于生活之上,轻轻松松/就理解花和沉默事物的语言。”16波德莱尔对生活的迷醉,又带来他阴郁的诗风。他将妓女、老妇人、腐尸、痛苦的大海写进诗中,这些形象也是他生存状态的写照。在《巴黎的忧郁》 ( Le Spleen de Paris)的跋诗中,波德莱尔写道:“我爱你,下流的都市! 妓女/和强盗,你们如此频繁地带来快活/世俗的庸人们对此却不懂得欣赏。”17阴郁的风格是后来颓废派统一的制服,也是象征主义的基本色调。波德莱尔在继承戈蒂耶、巴尔扎克(比如他的《驴皮记》)等人的阴郁风格的基础上,强化了阴郁的美学价值。在他对美的新定义中,可以发现阴郁具有相当重要的特征:美就像是一个女人的头,“它有一种热情、一种生存的欲望,又混合着一种相反的辛酸,好像来自贫穷或者绝望。神秘、遗憾也是美的特征。”18
从阴郁的风格又可引出第五个影响:反常的语言。反常的语言相对的是古典主义(以及一些浪漫主义作家)正常的语言。正常的语言选用正派、积极的词语,选用通常的词义。波德莱尔发展出一种对语言的破坏性用法,它故意使用邪恶的、消极的词语,而且在他的诗中,正派的词语在消极的语境中,也往往会发生词义的扭曲,发生同化作用。还以《巴黎的忧郁》的跋诗为例,诗中这样写巴黎:“那里所有的恶行都像花朵开放。”敏感的读者会想到《恶之花》这个题名与一个地名的联系。于斯曼( Joris-Karl Huysmans)曾称赞波德莱尔:“他的语言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拥有那种美妙无比的力量,能以表达上的一种奇怪健康,来确切指出疲倦的精神和忧伤的心灵那最不可捉摸、最战栗的死气沉沉的状态。”19所谓用“奇怪健康”的语言来表达心灵的忧郁,正说明波德莱尔对正常语义的扭曲。这种语言让词语具有了张力,拥有了非凡的力量。因为迷醉的心理和阴郁的风格,波德莱尔还采用了一种重章叠句的句法形式,一种并列的语法结构,用来加强感受的强度。在《陶醉吧你》 ( “ Enivrez-vous” )这首散文诗中,诗人写道:“你就需要向风、向海浪、向星星、向飞鸟、向时钟,向所有逃遁的,向所有呻吟的,向所有滚动的、向所有歌唱的,向所有说话的,询问是什么时间了。”20句中不仅有繁复的并列,而且“向”字的重复,“向所有”句型的重复,给人一种歇斯底里的、不能自已的感受。魏尔伦曾说:“波德莱尔在典型的状态下表现神经过敏的个体。”21这种语言以及其表达的感受,其实在魏尔伦、于斯曼等人那里也同样存在。
第六个影响是诗律解放。反常的语言也会对诗律形式产生新的要求,规则、整齐的诗行无法完全满足混乱、挣扎的诗思。波德莱尔在《恶之花》的前言的注释中,对新形式作了思考。他渴望诗律也能像他的语言一样具有新的破坏性的力量,实现的办法是诗律与内心的重新结盟,他曾作如下的思考:“诗怎样通过一种韵律触及音乐,这种韵律的根在人的灵魂中扎下,比任何古典的理论所指示的都要深。”22他也发现了音乐的重要性,音乐应该也来自人的灵魂。波德莱尔当时应该看到传统的亚历山大体已经失去了内心情感的依据,重新取得这种依据必然要打破亚历山大体的严格框架。基里克( Rachel Killick)发现:“ 《恶之花》的主要音律是十二音节的亚历山大体,这法语诗律典型的音律,伴随着少见的八音节的诗行和极少见到的十音节的诗行。与这些偶数音节的诗行一起,波德莱尔还使用了极其有限的奇数音节的诗行,绝大多数与亚历山大体交替使用。”23波德莱尔与后来的卡恩、维莱-格里凡等人相比,确实在诗律解放上迈得步子不大,基本还是思考诗律放宽的问题,但是他对诗律的新态度,则成为后来年轻诗人的榜样。
上面谈到的六点,并不是全部的内容,而是比较后得到的更为重要的内容。后文对颓废派和象征主义理论的论述,也会经常与波德莱尔的这六点进行比较。可以将这六点简称为波德莱尔颓废六事。这六事已经大致指出了后来颓废派和象征主义的发展方向。
三、波德莱尔对19世纪80年代初颓废文学的影响
在颓废文学的发展上,布尔热( Paul Bourget)是一位预言家。他让颓废文学受到的关注更多了。 1881年布尔热在《新评论》发表《当代心理》的系列研究论文,该年11月的文章就是献给颓废文学的。布尔热注意到了波德莱尔寻求“病态和人工的东西”,而且偏好“比其他事物更能激发我们身上具有的在感受上阴郁的东西”24。这两条,一条与波德莱尔的感受力有关,一条与阴郁的风格有关。为了获得超自然的感受力,波德莱尔敢于使用一些非常的、人工的手段,这也是自戈蒂耶以来,诗人和批评家都注意到的。布尔热这里的判断比较可靠。另外,文中还断言波德莱尔是“颓废的理论家”,这种判断无疑是一种历史拐点,它已经将波德莱尔视为颓废文学的先驱。尽管巴雷斯对布尔热的这篇文章有所批评,但是他曾称波德莱尔为“新艺术的先知” ( prophète d’un art nouveau)25,这未尝不是布尔热的影响。
布尔热的文章最重要的地方,是对颓废理论的思考。在他之前,很多人讨论过颓废,但什么是颓废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解。似乎颓废的含义并不需要特别的解释。颓废意义的固定,对颓废文学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人们一直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那么颓废就不可能成为一种风尚。布尔热的文章第四部分,小标题为“颓废的理论”,它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审视:“颓废这个词,人们通常指的是一种社会的状态,它创造了数量相当大的不适于做公共生活的事务的个体。”26也就是说,如果积极参与社会分工,那么这就是进取的,相反就是颓废的。颓废本身含有破坏原有的功能和秩序的意思。从布尔热开始,颓废的一个重要的含义被理解为远离社会,无所事事。在于斯曼的《逆流》 ( A Rebours)中,人们最初读到的德塞森特先生( Jean des Esseintes) “无论他尝试什么,无边无际的厌烦始终压迫着他”27。德塞森特身上的这种厌倦世事、离群索居的个性,在批评家保尔·布尔德( Paul Bourde)的文章中,还被上升到道德层面,做了更具体的评价:“它道德面孔上的特征是对大众表露出的厌恶,大众被看作是极其愚蠢和平庸的。诗人为了寻求珍贵的、罕见的和微妙的东西而离群索居。”28
颓废具体到文学中,指的是文学内部功能和秩序的解体。每个部分如果放弃它的功能,那么文学作品就无法成为一个整体。布尔热说:“颓废的风格是这样一种风格,那里书的统一性解体了,以便让位给页面的独立性,而页面也解体了,以便让位给语句的独立性,语句再让位给词语的独立性。”29语句和词语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文学的颓废。可是这里会有一个误解。如果语句和词语都拒绝为整体服务,文学的整体不再存在,也就没有文学,颓废文学毛将焉附? 布尔热的解释还有一些缺陷,这种缺陷在后来的批评家中得到了延续。比如拉布吕耶尔( Labruyère)曾主张:“颓废者并没有思想。它不想有思想。它更喜欢词语;当它找不到词语,它就创造词语。”30所谓没有思想,其实就是看到词语的无政府状态与思想的矛盾。这似乎是最早的文本解构主义的思维。但这并不是实情。无论波德莱尔的诗作,还是后来的颓废派,思想或者主题仍然存在。颓废文学只是在反崇高、反直接言说的道路上发展,这是一种表达和风格上的转向。其实对于这一点,布尔热并非没有看到,他敏锐地注意到了颓废带来了晦涩的诗风:“它们导致了词汇的改变,词语的过分细腻,这将给将来的那几代人带来难以理解的风格。”31这里触及了波德莱尔颓废六事的第四条和第五条。
该文对颓废文学有褒有贬,但贬多褒少,颓废文学被看作是没有未来的文学。但布尔热的文章还是吸引了一些人注意这类文学在当时的发展。魏尔伦就是这样的一位,他不仅从事颓废文学的试验,而且他的试验也被别的批评者注意,汇入19世纪80年代的颓废洪流之中。
魏尔伦1882 年在《现代巴黎》 ( Paris moderne)上发表《诗歌艺术》( “ Art poétique” )一诗。尽管这时兰波早已离开他,前往国外游历,但是与兰波的交往,让魏尔伦有机会从巴纳斯派向颓废诗人转型。《诗歌艺术》就是他这一时期诗学思想的缩影。魏尔伦早年受到过波德莱尔的影响,他曾称赞波德莱尔“卓越的纯粹性”,认为这位导师“在文学最完美的荣耀中占有一席之地”32。魏尔伦在《诗歌艺术》中首先讨论诗的形式问题:
音乐要胜过其他的一切,
特别是这种喜欢奇数的音乐33
这种奇数音乐,往往表现为十一音节的诗行。在波德莱尔的诗中,已经出现过奇数音节的诗行,基里克将波德莱尔看作是魏尔伦的老师,指出波德莱尔“指示了魏尔伦和象征主义者们的音律试验”34。实际上,雨果、邦维尔( Théodore de Banville)也同样做出了示范。波德莱尔并不是唯一的影响源。文学形式的颓废已经有了一些传统,魏尔伦将要给这个传统带来更丰富的节奏效果。
魏尔伦接着讲词语。不同于波德莱尔采用反常的词语,《诗歌艺术》的作者更偏好含糊的用语:
你在选择词语时
也不要将错误完全避免:
最忧郁的歌最可贵,
因为含糊加入确切中间。35
过于确切的词语,可能会限制意义的表达。其实这种见解背后,是意义的概念发生了更改。以前,意义是固定的,诗作的达意功能非常强。到了19 世纪中后期,意义被思想代替了。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曾经区分过观念和思想。观念就是固定的意义,思想则存在于语言之中,又能越过它,“不可表达”36。这种思想是感受的某种形式,或者寄寓在感受中,在魏尔伦的诗中,它与“微妙的色调”关系很近。在这四行引文中,魏尔伦肯定用错的词语带来的新奇的意义,也肯定含糊的词语。因为思想“微妙的色调”很难装在确切语言的容器中。这种看法与波德莱尔反常的语言论是声气相通的。
魏尔伦还将“微妙的色调”与“梦想”联系了起来:
只有微妙的色调把梦想
连上梦想,把长笛配给号角。37
梦想在句中是什么意思呢? 是理想? 还是梦幻? 通过上下文判断,更有可能是梦幻,但不是无意识的梦幻,而是与幻想相关。这里面强调的是丰富的内在生活,魏尔伦本人后来也做过解释,他所说的“灵魂、精神和心灵的三重表露”就是这种梦幻的具体含义。38 这种论述与波德莱尔颓废六事的第一条的感受力和第四条的神秘风格都有关系。
魏尔伦的这篇诗作,总的来看,就是阐述颓废的美学。它发表后马上得到敏锐的批评者的注意。莫里斯后来加入象征主义运动,但在1882年他还无法接受这种诗歌原则,他在《新左岸》 ( La Nouvelle rive gauche)杂志上撰文讽刺魏尔伦。但魏尔伦和莫里斯不打不相识,他们变成了好朋友,《新左岸》杂志也成为魏尔伦的重要园地,这就为魏尔伦后来的颓废诗学活动做了准备。
在1883年,文学颓废的火苗继续蔓延,《新左岸》杂志发表了特雷泽尼克论诗人科佩( François Coppée)的文章。特雷泽尼克是《新左岸》的主编,他注意到科佩的颓废思想“虚弱、有点造作,难有活力”39。这谈的是科佩的病态感受力。但特雷泽尼克并不像布尔热一样指责颓废,在他那里颓废似乎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独立地位的风格。他指出:“他希望显得被激情压垮了,或者被我们的颓废创造的病态压垮了:厌倦、忧伤、忧郁;他在呻吟中比在努力中找到了更多的魅力。”40这里出现的“颓废”一词,是继布尔热之后,该词在法国诗歌圈里非常重要的一次重现,它将1881年到1884年的颓废文学的讨论连成了一条线。特雷泽尼克也成为魏尔伦的支持者,他认为魏尔伦是波德莱尔的“直接信徒”,这说明他对颓废文学的起源相当清楚。他还具体分析了二人的具体联系:“他从这种危险的范例中得到了他闻所未闻的反常的精致,他的深刻,他的独特性;他有古怪的类比。”41这里的论述似乎超出了波德莱尔颓废六事的范围,不过,反常的精致,一方面触及了一种雕琢的诗风——这显示出魏尔伦作为巴纳斯诗人的特征——另一方面,则与反常的语言有一定的关系。最后谈到的“古怪的类比”,实际上是“古怪的象征”。在当时的不少批评家那里,类比与象征是等义的。比如维莱-格里凡曾有过“人类小宇宙与世界小宇宙的神奇的类比”的提法42,即是如此。特雷泽尼克还发现魏尔伦的反主题的倾向,他指出:“因为微妙,思想消失了。诗中有和谐,但是却不愿再说任何话。”43这种判断有道理。魏尔伦在将主题转向情调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随着魏尔伦在颓废文学中地位的加强,随着越来越多的诗人和批评家开始谈论颓废的问题,颓废将真正成为一种美学风格,颓废派也将真正缔造。而这一切,要从1883年8月开始。
1 Sutter Laumann, “Les Décadents”, La Justice, 7 (13 septembre 1886), p. 2.
2 Désiré Nisard,Études de mœurs et de critique sur les poëtes latins de la décadence, tome 2, Paris:Librairie de L. Hachette, 1849, p. 316.
3 Ibid. , p. 317.
4 Arnaud Laster, “Hugo, cet empereur de notre décadence littéraire”, Romantisme, 42 (1983), p. 101.
5 J. Babbey D’Aurevilly, “Les Misérables”, Le Pays, 195 (14 juillet 1862), p. 3.
6 Émile Verhaeren, Impressions, Paris: Mercvre de France, 1928, p. 21.
7 André Barre, Le Symbolisme,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68, p. 53.
8 Novali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trans. M. M. Stolja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 26.
9 Charles Baudelair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1, ed. Yves Florenne, Paris: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6, p. 700.
10 Emanuel Swedenborg, Heaven and Its Wonders and Hell, trans. John C. Ager, West Chester:Swedenborg Foundation, 1995, p. 76.
11 Charles Baudelair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3, ed. Yves Florenne, Paris: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6, p. 573.
12 Ibid. , p. 1337.
13 T. S. Eliot,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51, p. 422.
14 Charles Baudelair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3, ed. Yves Florenne, Paris: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6, p. 1261.
15 Charles Baudelair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1, ed. Yves Florenne, Paris: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6, p. 768. 中文诗为笔者自译。后文不特别注明的译诗,均为笔者自译。
16 Ibid. , p. 767.
17 Charles Baudelair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3, ed. Yves Florenne, Paris: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6, p. 126.
18 Ibid. , p. 1219.
19 于斯曼:《逆流》,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87页。
20 Charles Baudelair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3, ed. Yves Florenne, Paris: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6, p. 87.
21 Paul Verlaine, Œuvres posthumes de Paul Verlaine, tome 2, Paris: Albert Messein, 1927, p. 4 .
22 Charles Baudelair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1 , ed. Yves Florenne, Paris: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6 , p. 1026.
23 Rachel Killick, “ Baudelaire’s Versification: Conservative or Radical?” ,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audelaire, ed. Rosemary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2.
24 Paul Bourget,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 La Nouvelle revue 13 (nov. 1881), p. 415.
25 Maurice Barrès, “La Folie de Charles Baudelaire”, Les Taches d’encre, 1 (novembre 1884), p. 25.
26 Paul Bourget,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 La Nouvelle revue, 13 (nov. 1881), p. 412.
27 于斯曼:《逆流》,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28 Paul Bourde, “Les Poètes décadents”, Le Temps, 8863 (6 août 1886), p. 3.
29 Paul Bourget,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 La Nouvelle revue, 13 (nov. 1881), p. 413.
30 Labruyère, “Le Décadent”, Le Figaro, 263 (22 sep. 1885), p. 1.
31 Paul Bourget,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 La Nouvelle revue, 13 (nov. 1881), p. 414.
32 Paul Verlaine, Œuvres posthumes de Paul Verlaine, tome 2, Paris: Albert Messein, 1927, p. 157.
33 Paul Verlaine,Œuvres poétiques complètes, établie par Y.-G. le Dantec. Paris: Gallimard, 1962, p. 326.
34 Rachel Killick, “ Baudelaire’s Versification: Conservative or Radical?” ,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audelaire, ed. Rosemary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65.
35 Paul Verlaine,Œuvres poétiques complètes,établie par Y.-G. le Dantec. Paris: Gallimard, 1962, p. 326.
36 J. W. V. Goethe, Maxims and Reflections, trans. Elisabeth Stopp, London: Penguin, 1998, p. 141.
37 Paul Verlaine,Œuvres poétiques complètes, établie par Y.-G. le Dantec. Paris: Gallimard, 1962, p. 326.
38 Paul Verlaine, “A Karl Mohr”, La Nouvelle rive gauche, 6 (15 décembre 1882), p. 2.
39 Léo Trézenik, “François Coppée”, La Nouvelle rive gauche, 52 (26 janvier 1883), p. 3.
40 Léo Trézenik, “François Coppée”, La Nouvelle rive gauche, 52 (26 janvier 1883), p. 3.
41 Léo Trézenik, “Paul Verlaine”, La Nouvelle rive gauche, 54 (9 février 1883), p. 4.
42 Francis Vielé-Griffin, “Les Poètes symbolistes”, Art et Critique, 26 (23 novembre 1889), p. 402.
43 Léo Trézenik, “Paul Verlaine”, La Nouvelle rive gauche, 54 (9 février 1883), p.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