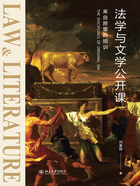
原罪烙印——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耶稣站起身来向女人走去,立刻被愤怒的市民、不怀好意的法利赛人以及凶狠残酷的文士所包围。他平静地指着地上匍匐的女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
——《新约·约翰福音》(8:7)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旧约·出埃及记》(20:13-20:17)
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但他的言谈举止却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依赖于该种文化才有意义。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重新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来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了,羊儿吃了,长出毛来,你才能用羊毛做出一件新大衣。在此期间,你必须经过若干个世纪的野蛮状态。
——〔英〕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
时代背景
持续千年的中古时期,希伯来—基督教文明在西方一统天下,认为人类祖先因违背上帝诫律偷食禁果后获取惩罚,继而遭受永劫之苦。由于人类祖先具有原罪,原恶就蛰伏于人类本性之中。如此,古希罗文化中人之“原欲”就转变为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原罪”,这种原始欲望既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活力之源,也是其沉沦于感官地狱的原始驱动,人类在繁衍与毁灭、创造与破坏、美德与邪恶间轮回辗转,永无停息。如《刑法与文学公开课》第一辑《来自原欲的呼唤》所述,古希罗文化中,原欲以其本色的面目出现,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与法学思想也对人类个体价值充分认可,对自然释放的人之原欲热烈赞美;而在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原欲被打上了原罪的烙印,不时敲响警钟,告诫人类应当不断涤荡罪恶、接近圣洁。
统一后的罗马帝国穷兵黩武,追求法律与集权的强盛与完美。反映在刑法思想层面,古罗马人以务实的精神承袭了古希腊人尊崇的自然法观念,刑事处罚逐渐介入宗教、城邦、家庭、个人四个领域,该种司法模式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蔓延至整个欧洲。《十二铜表法》(公元前450年前后)被公认为罗马刑法典之鼻祖,其中第八表(私犯)与第九表(公法)即为罗马刑法之渊源。《十二铜表法》规定了至详的刑法规范,现代刑法基础理论几乎在《十二铜表法》中均有所涉猎,其中包括犯罪概念的表述、犯罪故意与过失的划分、犯罪阶段与犯罪停止形态的界定、犯罪责任要件(刑事责任年龄)的满足等;另外,《十二铜表法》还建立了疑罪从无、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处以死刑等司法原则与制度。[7]然而,众所周知,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均臻于完美的《十二铜表法》未能阻止罗马帝国的轰然坍塌。
究其根源,习惯于以武力征服获取荣耀的古罗马人,其文化底蕴却相对贫瘠。征服古希腊后,面对希腊人强调个体本位的原欲型文化内核,古罗马人感到无比新鲜与刺激,很快将其演绎为对肉欲与物欲的放纵。这种直白、浅显的文化解读直接诱发了罗马帝国末期贵族阶层的侈靡颓废,并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对原欲的狂热追逐之中。
一位马赛诗人对5世纪古罗马的堕落作出如此下描述:“帝国境内……均滑向罪恶深渊,他们将酗酒当作时尚、将通奸看作荣耀,却给节制与美德蒙上羞耻的面纱……奄奄一息的罗马帝国正在迈向死亡。”[8]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年)[9]亦描述过罗马人酒神节的狂欢情景:“狂欢而又放荡……人群将巨大的男性生殖器摆上马车,高声歌唱、招摇过市;城中身份最贵重的妇人将花环一圈圈挽上它的根茎,纯洁的处女们伸展双手向它祈祷……这种堕落可怕的仪式,恐怕连一个妓女遇见也会掩面离去。”[10]民间醉生梦死,皇帝的德性也颓败之至,塔西陀的《编年史》中记载了尼禄皇帝荒诞离奇的丑态:“装扮后的尼禄变成了一名奴隶,侍从们拥簇着他在妓院与酒肆中游荡。他们专门偷窃商店里的东西,并丧心病狂地随意袭击路过的百姓。”[11]帝王如此,贵族们自然亦步亦趋,其奢靡生活被罗马诗人马蒂里尽收眼底:“绿衣贵族坦卧绸塌,千娇百媚的侍妇宽衣解带卧在其侧、轻摇绿扇。少奴用陶瓷金板挥杆蚊蝇,女摩挲师为他进行全身推拿。失势的奴隶紧张地等待着他的弹指信号,敏捷地将头靠近,安静地吞下他的小便,专注地凝视着尊贵荣耀的主人。”[12]在这样一幅幅糜烂堕落的图景中,人类的耻感与罪感荡然无存,这正是罗马帝国末期危机四伏的表征。最后数个世纪中,罗马帝国饱经战火蹂躏,日耳曼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惨遭荼毒。“此时,一个来自遥远、陌生国度的声音由远及近,它是那样空灵、温柔、微弱,与罗马世界的粗鄙张扬、醉生梦死具有天壤之别。这首梦幻般的圣曲以恬美的音符、舒缓的旋律感动了辗转于苦难中的人们,以纯洁的信仰对抗罗马帝国的物质主义,以理性的禁欲节制抵御罗马帝国的放纵骄奢。质朴、虔诚的日耳曼民族挥动着‘上帝之鞭’抽打着彪悍凶猛的罗马人,摧毁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13]
欧洲人立于古罗马的废墟上发出感慨,认为罗马帝国的毁灭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从文化层面考察,则应归咎于古罗马人对原欲型文化的过度推崇与沉溺,导致群体理性的湮没与个人原欲的泛滥,二者之间的制衡关系失调。文学作品《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对古希腊神话中放纵情欲的众神厉言诅咒,认为是他们造成了古罗马人的放荡不洁;在此批判基础上,奥古斯丁虚构出至善与至美的永恒世界,引导人们放弃对现世物欲、肉欲的追求,皈依充满希望与光明的彼岸世界。[14]欧洲人在惊惧与哀伤中开始反思,试图寻找救赎自我的途径,逐渐意识到人类内心原欲的邪恶,渴望以理性来与它抗衡。这种群体性心理为来自东方的希伯来宗教文化的渗透与蔓延提供了精神沃土——在罗马帝国轰然崩塌的惨痛教训面前,希伯来宗教文化关于人之“原欲”即“原罪”的警告具有无比雄辩的说服力,基督教文学所提供的清新、圣洁的彼岸之景亦给西方人失序的心理注入了无穷希望。[15]他们充满虔诚地将上帝迎入灵魂的圣殿,希望以上帝的慧目来监管内心的邪恶,加重人性天平上的理性砝码,遏制原欲的涌动。可见,上帝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教会刑法在欧洲的盛行,是出于特定时期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正是群体性心理需求促成了强调抑制原欲、注重精神寄托、鼓励群体本位的教会刑法的萌芽,教会刑法逐渐发展为严密的逻辑体系,与罗马法、日耳曼法并列成为欧洲近代三大法律渊源。[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