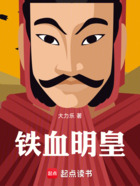
第19章 门阀
作为陪都,南京虽然有一套完全参照京都的官员体系,但是并不完善,缺额很大,这就为朱由菘省了不少麻烦。
直接提拔那些低阶官员,大多都是一次性官升好几级,更多是直接从翰林院挑选候补官员。
这种看似荒诞的提拔,在其他大臣眼中就是胡闹,却显示了朱由菘的大智慧。
今天还是八品,九品的低阶官员,明天就是三品,四品,一天就走完了其他大臣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仕途,可谓一步登天。
这个让他们一步登天就是陛下,他们怎么能不忠于陛下。
最主要是这些小官员没有进入党争的核心阶层,也没有任何威望,他们能有今天的位置,完全是朱由菘一句话,这就便于控制。
至于翰林院的候补官员,接到圣旨更是感动老泪纵横。
明朝中期开始就不缺官员,就像大学生毕业一个道理,那些考上功名之人,只能进翰林院成为候补官员。
大多数时候,这一等就是好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都在候补。
现在皇帝给他们机会转正,直接让他们原地起飞,满足寒窗十年的梦想。
当然朱由菘也并不是见人就提拔,而是让锦衣卫调查一番,东林党之人首先排除,最好是无党派且身家清白的寒门子弟。
一直有个误区,大家一直觉得寒门贵子都是天纵之才,门阀大族多出纨绔。
其实综合素质和能力来讲,门阀子弟确实是要强过寒门,这并不是门阀基因有多好,只是教育、信息、资源还有人性等因素。
因为主流的宣传,往往会放大优点和缺点,二代很烂就会放大,以偏概全,觉得这一群体都是这样,同样的,寒门子弟优点也会被放大,就形成了一个管中窥豹的误区。
唐朝以前,华夏基本都是完胜周边,就连相互内斗的战国和三国,周边都老老实实,但是唐朝以后,基本就不行,经常让周边做大做强,最后吃掉自己。
黄巢有一定原因,踏碎公卿骨,也让以后得朝代的皇权没有了门阀的牵制。
至于什么尚武精神的缺失,或者什么重文轻武,再或者北方少数民族生产力提高,冶铁技术发展,甚至说马凳的普及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怎么说呢。
唐以前的门阀有些类似于诸侯,在当地威望很高,拥有很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几乎可以抗衡皇权。
唐以后的门阀是皇帝册封的勋贵,完全依附于皇权,每个朝代时间久了也会形成门阀,大明也不例外。
不过唐以后得门阀质量和持久远远不如以前,以前百年王朝,千年门阀,唐以后的门阀基本是和皇权盘根错节相互依存,王朝覆灭,门阀灭亡。
唐以前的门阀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甚至联合起来可以制衡皇权,两个之间,关系微妙。
之后的门阀,严格意义上讲,都不算是门阀,只能算是公司创业成功的股东,或者用既得利益者更形象。
既然依附于皇权生存,自然不可能制衡皇权。
明朝的门阀,大多都是勋贵,至于文官,已经无法形成门阀,隋炀帝为了限制门阀,创办科举,唐宋发扬科举,明清达到巅峰,几乎所有文官基本都需要通过科举,不说逢进必考,基本95%官员都需要通过科举。
这就是所谓的流官制,哪怕你做的再大,就算做到内阁首辅,文官一把手,只要家族人科举上没有上岸,基本无法实现完成权利的交接。
当然内阁一把手弄几个家族子弟进入仕途也是很容易,但是没有功名在身,很难身居高位担任要职。
红楼梦贾府的衰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文官中权利的传承,只能达到10%。
这一点甚至好过现在。
勋贵是有爵位,世代罔替,几乎是100%传承,看似门阀,却根本不是门阀,这和唐朝之前的门阀完全不一样。
文官没办法像勋贵一样传承爵位,就会抱团,形成文官集团,或者党派。
商鞅变法以后,秦制确立,绵延两千年,这两千年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称为封建王朝,而是特有的皇权专制。
封建封建就是分封建制,有些类似于西周,周天子虽然是周王朝的一把手,但是势力范围只有镐京附近,没有权利干涉其他诸侯的领地。
这一点有些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国王不能控制全国的城邦,只能控制都城附近。
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秦制就不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换句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我全要!
商鞅变法核心就是收天下之权于皇帝,包括贵族、官员、百姓、奴隶都是皇帝的私有物品。
除了对皇帝一个人大利好,对其他人都是大利空,这也就得罪了除皇帝之外的天下人,这也注定了商鞅一定不会善终,百姓和奴隶没办法把商鞅如何,但是贵族和官员却可以。
商鞅铸就的秦制,对于皇帝实在太香了,这也导致,以后所有造反上位的新皇帝都抵抗不住诱惑,最终选择秦制,都以为自己打好上一个王朝灭亡的教训的补丁就可以江山万代。
不断地打补丁下,最终诞生了满清这样打满补丁的怪物。
这也是未来两千多年,所有的王朝基本都逃不过历史周期律的根本原因。
除非这个王朝的皇帝掌握的军队可以消灭天下人,这就需要科技,但是秦制王朝控制思想和自由,无法诞生科技,只有在生产中偶尔发现的技术。
很多人一直有一个误区,觉得寒门子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金榜题名,成为朝廷官员就会为底层人做些事,因为他来自底层,知道底层人的心酸和苦难。
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皇权制度的特殊性,让他掌握权利的那一刻起,就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就顺利从羊变成了狼,无关人性,而是制度。
正是因为寒门来自于底层,他更懂得如何整治底层。
这一点好像工厂里面辛辛苦苦打螺丝的牛马,一旦当上了领导,他一定明白打工人的苦,难道就会体谅那些底层螺丝工?
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只会在更高领导面前建议如何更有效的管理。
这些从底层爬上来的领导,知道你会如何摸鱼,知道那里是管理盲区,知道你怕什么,他会打上补丁,让你更难受。
而不是和你一起对抗公司的更高领导,因为他成为领导那一刻起,你们已经不是同类。
上岸先斩意中人,很好说明了这个分水岭,因为上岸的那一刻起,立场就不一样!
在皇权治世下,这种对抗更加尖锐和直接!
寒门贵子,十年寒窗,苦了十年,穷了十年,一旦成为流官,就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穷怕了,更会疯狂敛财,当然也有清流,比如海瑞、于谦。
纵观华夏历史,所有官员加起来何止百万,但是海瑞有几个?占比率不到万分之一!!!
从数学上讲,这就是小概率事件,所谓小概率事件还有一个名称——几乎不会发生的事件!!!
以朱由菘的认知,自然明白皇权的缺陷,无论用任何人都会糜烂,何不用听话好控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