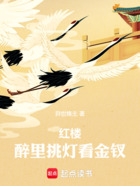
第10章 一篇策论,三堂会审
国子监率性堂内,空气比晨钟敲响前更为凝滞。
不同于初次授课时满堂喧嚣后的沉寂,今日的死寂中掺杂着一种等待宣判的压抑感。
案几之间偶尔传来细微的纸张翻动声,或是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轻响,都带着一种生怕惊扰了什么的谨慎。
崔令仪高踞讲案之后,鸦青色的直裰在晨光中沉静如渊海。
她手中执着一卷《春秋繁露新注考异》,并未翻看,只是用那修长的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叩击着微黄的宣纸书口,发出极轻微的叩击声,如同古殿檐角雨滴落玉盘,在死寂的堂中清晰可闻。
她目光垂视,仿佛专注地欣赏着自己手背清晰的骨节轮廓,那份漫不经心的姿态,却比任何严厉审视更让人心头发紧。
案头,整齐堆放着一叠墨迹未干的考卷,正是昨日策论考校之果。
司业陈景明身着一件半新的靛蓝补服,沉默地坐在讲案稍下首的偏座上,手中也捏着几张考卷。
他神色平静,只在偶尔抬眼看崔令仪翻阅卷宗时,眼底深处掠过一丝审视。
气氛如同绷紧的弓弦。
所有监生都埋着头,或装作用心温书,或死死盯着自己桌案一角,大气不敢出。
刘承业更是将脸几乎贴在了书页上,试图将自己藏匿起来,但那粗重的喘息声还是暴露了他的躁动不安与羞愤难当。
他能感觉到周遭似有若无的、带着幸灾乐祸意味的目光如针刺般扎在脊梁上。
终于,崔令仪翻检考卷的手指停在了一份卷面上。
她并未抬头,只以指尖轻轻点在上面。
“刘承业。”
声音不高,甚至没有刻意加重。
刘承业却如同被烙印烙了一下,猛地一颤,身体僵硬地慢慢抬起,额头瞬间冒出一层细密的冷汗。
崔令仪终于抬起眼帘,那双琥珀色的眸子无喜无怒,却带着一种洞穿人心的力量。
她随手抽出一张显然是刘承业的答卷,上面的字迹狂放、墨迹深浅不一,多处有涂改的污迹。
她将答卷略略展开一些,好让前排的监生也能看清那份混乱的字迹。
“‘牝鸡司晨,祸国之始’?”
崔令仪的声音依旧平静,只是将刘承业文中那句露骨抨击她性别的言论清晰地复述出来,“‘祖法崩坏,士林蒙羞’?通篇戾气滔天,引据却只止于《女诫》、《女则》之类闺阁蒙训之书?”
她略作停顿,目光像冰冷的剃刀般刮过刘承业那张惨白的脸:“你此番答卷,论题何在?文理何在?通篇只见‘性别’壁垒森严,不见丝毫‘民生’关切!究其根本——”
她的声线陡然下沉,带着冰雪的重量砸下,“不过一己私念受挫、面目难存之刻薄怨怼,披了张圣贤大义皮囊的狂悖妄言罢了!字字咆哮如雷,句句刻薄诛心,哪里见半分‘为国忧民’的本心?哪里配言一个‘儒’字?!”
“哐当!”一声重响!
刘承业面无人色,猛地起身后退,带倒了身后的硬木方凳!
巨大的声响在死寂的堂内如惊雷炸裂!
他浑身剧烈颤抖,牙齿咯咯作响,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抽气声,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崔令仪那精准的宣判,将他最后一点强撑的遮羞布撕得粉碎!
崔令仪的目光只在他身上停留了一瞬,便漠然地移开。
“陆明远?”
一个清瘦的江南监生闻声猛地抬头,脸上掠过一丝讶异与不安——他可是最初支持崔令仪的南方学子之一。
崔令仪展开他的考卷,字迹清逸飘洒,内容旁征博引:
“《逍遥游》有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国事如烹鲜,无为而治方是大道?民如蜉蝣,顺其自然?国之盐政重器,竟托于无为之手?”
她声音陡然转厉,如同寒铁交击:“尔等江南俊彦,素以通晓经典、胸怀天下自诩!然国难当头,盐课崩解,民生如陷水火。尔不思‘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之务实,不虑‘除苛捐、清吏蠹’之急策,却在此高谈‘无何有之乡’、‘彷徨乎无为其侧’的黄老玄虚!”
她冷笑一声,眼中寒芒如电,直刺陆明远:“这等避重就轻、空谈误国之论,与昔年何晏、王衍之辈以清谈葬送晋祚,又有何异?这非是真逍遥——乃是怯懦!是对社稷苍生的推诿!”
陆明远脸色瞬间惨白,身体僵硬,嘴唇哆嗦着,却一句辩解也吐不出来。
支持者的身份未能带来庇护,反被更精准地点中了学问空疏、逃避责任的要害。
堂内所有监生,包括原本惊恐万分的程景明,更是深深埋下了头。
崔令仪的打击对象并非仅针对不满者,更针对所有不合时宜、空谈误国的思想,无论南北!
那份冰冷无情的审视,无差别地笼罩着每一个人。
程景明感受到崔的视线仿佛扫过自己那份卷子,心脏骤停,冷汗浸透了后背,然而那批判并未落下。
他劫后余生般地瘫软在座位上,几乎虚脱,只剩下无声的庆幸与更深的恐惧。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死寂即将冻结所有思绪时,崔令仪翻卷的动作停顿在另一份考卷上。
那字迹端正而不失风骨,通篇布局严谨,行文稳健。
她的目光在卷首快速掠过,并未做长时间停留——卷中论点紧扣“安民之本在于开源节流、去冗除弊”,以“崇俭戒奢、清吏治、重农桑”为表,藏“苛政扰民如虎噬”、“蛀蠹盘踞漕粮虚耗”、“仓廪不实根基动”之针于棉絮之中,表述安全而务实。
崔令仪的指尖在卷尾最后一行字迹上划过——“治国若烹小鲜,急则烂”。
看到此处,她那紧抿的唇线,极其细微地向上牵动了一下!
这瞬间的微表情消失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几乎让人怀疑是光影的错觉。
她的目光旋即从这份考卷上移开,如同只是随手翻过一页无关紧要的旧纸。
贾琰低垂的眼睑遮住了眸底所有情绪。
他清晰地感受到了那道落在自己答卷上、短暂停留后又移开的目光,以及那几乎无法捕捉的唇角波动。
没有点评。
没有赞许。
更没有像刘程二人那般被当众凌迟式的剖析。
堂内的低气压持续盘旋。
崔令仪终于结束了所有的评阅,将最后几张未点评的卷宗合拢,轻轻置于案头,发出“嗒”的一声轻响。
这时,一直沉默旁观的司业陈景明缓缓起身。
他走到讲案旁,拿起了那份只得了崔令仪一个几不可察“微扬”的考卷。
他目光垂落,快速浏览着上面的内容,布满皱纹的手指无意识地捻着卷角。
那份卷面字字沉稳,滴水不漏,引经据典皆在安全范围之内,观点亦是老成持重之论。
片刻,他抬起眼,目光如古井深潭般投向坐在角落的贾琰,声音低沉平稳,只有两个字,却清晰地送入了贾琰耳中:
“尚可。”
再无多余评述。
语毕,他便将那份卷子复又放下,仿佛那只是万千卷宗中极为普通的一份。
“尚可”二字。
是认可其稳健?
是讽刺其藏锋?
还是仅仅一句无甚意义的官场客套?
陈景明的态度比崔令仪那一瞬间的微表情更加模糊难辨。
但贾琰面上依旧平静如水,只在陈司业目光投来的瞬间,微微垂首,做恭谨受教状,掩去了所有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