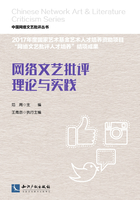
一、“后人文主义”的兴起及人文价值重建
20世纪末期,随着“后人类” (posthuman)社会的临近,“后人文主义”
(posthuman)社会的临近,“后人文主义” (posthumanism)随之开始成为频繁出现于学术话语和大众媒体的一个概念。
(posthumanism)随之开始成为频繁出现于学术话语和大众媒体的一个概念。
从“后人文主义”出现伊始,不但备受关注,同时对它的讨论和研究也在不断走向深入,最终使得“后人文主义”开始成为一个有能力横跨哲学、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医学、生态学、地理学、文学批评、电影研究、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等多种学科的极具阐述可能性也被认为是极具学术前景的学术话语 。当然,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学术话语。
。当然,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学术话语。
严格地讲,在西方学术界,“后人文主义”其实有两种尽管不乏含义的相关联性,但是也确实有着根本性区别的用法,一种可以被称为“工具性后人文主义”(instrumental posthumanism),而另一种则应该被称为“批判性后人文主义”(critical posthumanism)。之所以在学术讨论和媒体传播过程中对“后人文主义”的理解总是会有一些不必要的分歧,其缘由大概正是因为没有能够清晰地区分开这两种不同的“后人文主义”。简要解释一下,两者的区别是,“工具性后人文主义”肯定了人类自身被现代信息技术、生命技术所改变的事实并为此而欢欣鼓舞;相反,“批判性后人文主义”对“后人类”社会的到来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疑虑。
廓清种种概念和定义上的差异无疑有助于对“后人文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不难理解,“后人文主义”的出现,最直接的原因是表示对“人文主义”的种种不满以及反抗。也就是说,曾经积极促进了人类文明不断前行的“人文主义”,或许此时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绊脚石。事实正是如此。我们知道,“人文主义”之所以能够有能力把人类从中世纪神权的约束中解救出来,是因为理性的存在。从这个时候开始,理性取代了神性,成了新的人类形象的表征。应该承认,理性的到来,让人类史无前例地认识了自己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深入发掘了蕴藏在自身内部的能力、个性和诸多思想行为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人类在近几百年的时间里总是充满着自信。但是,也正是因为人的理性,从19世纪末以来却越来越表现出一种把人类逼上生存绝境的趋势和倾向。更悲观一点说,生存的困境乃至绝境已经在我们的周围悄悄蔓延开来。比如世界范围内的两次惨绝人寰的屠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的价值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虚无化等。稍稍回溯一下就可以发现,理性正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反思、批判“人文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后人文主义”则应运而生。
1976年,文化理论家伊哈布·哈桑 (Ihab Hassan)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演讲中说:
(Ihab Hassan)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演讲中说:
目前,“后人文主义”可能看上去是个含糊的新词,是时髦的标语,是不断复现的人类自我憎恨的另一个形象。但是,后人文主义也暗示着我们文化中的某种潜力,某种挣扎着逃脱沦为时尚的趋势……人类的形态——包括人类的欲望以及所有的外部表征——可能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因此必须要重新构想。500年的人文主义传统可能走到了尽头,人文主义蜕变成了一种我们不得不称为后人文主义的东西。
哈桑的这段话指明,“人文主义”终将被“后人文主义”代替的结局是无可挽回的。因此,我们就有理由把“后人文主义”纳入到我们的学术视野加以观照。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哈桑的这几句话里,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人类的形态——包括人类的欲望以及所有的外部表征——可能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因此必须要重新构想”,哈桑的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人文主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作为“人文主义”的批判者甚至是颠覆者而存在的,但是“后人文主义”绝对不能够被理解成“反人文主义”。“后人文主义”之所以不同于“反人文主义”,一方面表现在“后人文主义”不仅致力于批判和瓦解“人文主义”,同时还致力于在“人文主义”坍塌的地基上有新的建树,也就是哈桑所说的“重新构建”,但是我们也知道,“反人文主义”并没有如此的宏愿;另外,“后人文主义”所蕴含的建构性也就决定了,对“人文主义”的传统,它也绝对不会全盘否定、全然舍弃;相反,它会用批判的方式化“人文主义”的某些部分为己所用。也就是说,“后人文主义”其实也就是“人文主义”面对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现代高科技影响下的现实生活的自我反思、自我重构。尽管这种反思和重构里多少会有一点酸楚。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后人文主义”的“重新构建”和网络文艺的自我构建之间是否会有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恰恰是本文希望能够把握的。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一切还只是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