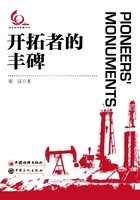
05 地质“侦察兵”拉开序幕
1979年1月,在上海浦江饭店召开的国家地质总局局长会议上,总局作出了在塔里木盆地开展油气普查工作的具体部署。
专家们认为,综合使用各种勘探手段,及时整理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是“多、快、好、省”地获取地质油气成果的不二方案,而优选勘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56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大部分为沙漠覆盖,中心部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人称“死亡之海”,边缘地区沼泽戈壁相间,交通极为艰难,地质研究程度很低,全区只作过1:1000000的航空磁测。1956年,新疆石油队在库车、喀什等地作过油气普查,原地质部石油综合研究队在西北部与南部库车、喀什等坳陷作过调查和综合研究。1977年提出的“突破喀什、准备和田、查清东部、探索中央”的部署方案,也只能作为一个宏观战略,由于缺乏具体资料,不能作为选择工区的依据。
国家地质总局根据国家石油工业发展的战略需要,认为塔里木盆地是寻找几个“大庆式”油田的含油气远景区,其中以西南坳陷区最好,塔东坳陷区也具有较好的找油前景,决定实施《塔里木盆地地质普查勘探设计方案》。基本原则是要从全盘着眼,分区规划,突破喀什,准备东部,探索中央。
3月初,所有参加塔里木盆地石油勘探会战的人员,不顾数千里长途跋涉的疲劳,群情激昂地开赴工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国家地质总局组建了塔里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康玉柱任队长。3月15日,大队领导组织全体职工召开塔里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出征塔里木欢送会。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大队长吕华致欢送辞。他说:“同志们,现在你们将带着党中央的嘱托,进军塔里木,这是你们的光荣。你们是我国地质战线上的一支特别能吃苦、敢啃硬骨头、能打胜仗的‘侦察兵’,希望你们不负重望,在塔里木盆地找到大油田……”
康玉柱代表塔里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致答谢辞。他说:“衷心感谢大队领导和全大队同志对我们热情隆重的欢送,感谢领导对我们的鼓舞和期待,我们决心牢记和发扬‘三光荣’精神,坚决完成任务,为在塔里木盆地找到大油田贡献自己的一切。请领导和同志放心,请家属们放心,我们要以优异的成绩向祖国汇报、向领导和同志们汇报!”
塔里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在锣鼓声中开拔了。在场的家属流着泪千叮咛万嘱咐:“你们在野外注意安全,别忘了给家里来信……我们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初春的南疆,天气乍暖还寒。但是地质队员热情高涨,一点也不觉得寒冷。
塔里木队首先在喀什坳陷挑选喀什背斜、明尧勒背斜及木什背斜开展了地质勘查和评价。为了确定普查井位,组成三个组,艰苦拼搏,对各背斜开展多条横穿背斜的路线勘查。
工区是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老职工形容当时的情景是:“每天二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
经过一个半月的拼命工作,提出了喀参1井、喀参2井、喀参3井井位建议。之后,为开展重力普查和地震测线提出了具体部署。
当时,我国对塔里木盆地的油气地质特征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相关资料,老一辈石油人认为塔西南是最有利的油气突破区。
4月初,康玉柱带领塔里木队,每天分四个小组,在喀什坳陷地青高山的木什构造、明尧勒构造、喀什构造开展构造检查,以便确定井位。横穿构造高山时,遇到第三系块状砂砾岩,五米至十米的厚度,无法越过。地质队员就用小镐刨挖脚坑,拉着绳索攀登悬崖。经过一个多月的构造检查,确定了喀参1井、喀参2井、喀参3井三个勘探井井位。
4月是喀什地区的风季,大风肆虐,帐篷搭不起来,队员只能住进山区牧民转场用的羊圈里。即使腥膻味熏得人作呕,也比躺在山风呼啸的野外好一点。
6月上旬,石油部副部长兼克拉玛依管理局局长李敬同志邀李奔到叶城,向李奔介绍了大量资料并商议今后部署方向。在一幅比例尺约为百万分之一的重力图上,李奔看到了十来个重力高。李奔心想,这些位置很好,特别是塔南跃进1号重力高,只要有决心克服困难,是可以进去工作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李奔随即向李敬副部长提出,请他协助。李四光部长对重力高很感兴趣,大庆油田就是在大同重力高上发现的。
新疆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后改称第三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指挥长李奔,副指挥长徐生道、吕华,技术负责人康玉柱研究决定,首先突破喀什坳陷。8月,责成442队、443队、644队在明尧勒、木什地表构造上进行地震技术方法试验及试生产,904队在和田河以西进行1:200000航空磁测,一物对喀什坳陷进行1:100000重力普查。为了解喀什坳陷—麦盖提斜坡—巴楚隆起的区域地质构造,沿叶尔羌河部署地震区域剖面,并在喀什地区进行地震概查,完成地震剖面430千米。通过上述工作,对喀什坳陷的形成、发展以及地层、构造都有了一些了解。
所有参加会战的队伍,思想觉悟都非常高,人人以大局为重,服务组织调动,克服一切困难。到达喀什后,本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立即投入生产。
从喀什到麦盖提斜坡至巴楚隆起的施工现场,戈壁平坦辽阔、一望无际。一簇簇发黄的骆驼刺闪着生命之光。戈壁滩上没有路,汽车在荒芜的沙漠上艰难地前进,在沙丘里蜿蜒曲折地穿梭,有些地段车轮辗压过去,浮土像水一样向两边飞溅。
队员们不顾天寒地冻,迫不及待地抓紧施工,在元旦深夜完成了喀参1井基础施工。4002井队打前站的同志们放弃元旦休息,顶着凛冽的寒风直奔麦参1井施工。物探、地震两个分队,在驻地立足未稳,就投入仪器性能试验。所有参战队伍全都铆足了劲,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要在这场石油会战中大显身手。
1979年初,陈飞鹏和康玉柱等同志研究确定了麦盖提斜坡上麦参1井井位,由一普4001井队负责施工。
1979年4月13日,由一普5012井队施工的喀参1井开钻。这是西北油田进疆的第一口探井,拉开了西北油田在塔里木盆地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序幕。
1979年6月至7月,韩军等同志到乌鲁克恰提勘测剖面。乌鲁克恰提是帕米尔高原小城乌恰县最西边毗临边界的一个乡,距县城有200多公里,居民以柯尔克孜族为主。
乌鲁克恰提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盆地,初夏的植被将大地装点成一块绿色的地毯,水草丰茂的草原上零星散落着帐篷,随处可见冒着小水泡的泉眼,积水中有小鱼自由自在地游动。高寒山区气温较低,尤其是昼夜温差很大,夏季早晚时甚至能感到阵阵凉意。每天出去勘测剖面的地质队员坐在大卡车上,被风吹得脸色发青、嘴唇发紫。
毕业分配来的内地大学生哪里见过这样的环境,他们被大自然的广博与苍凉所震撼,也为自己的渺小与卑微而悲哀,有一种要流泪的感觉,有一种想要表达宣泄的冲动,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说些什么。
分队岩相组组长阙延强是一位很有生活张力的人,充满了朝气,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创造出生活的激情。
阙延强做事很有条理,做每件工作都会事先制订出周密的计划,画出工作的流程。他那种执着向上、热爱生活、特立独行的性格,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大大出乎地质员工的意料。干旱缺水,工区的饮用水都是汽车从几十公里外拉来的,水比油还贵。戈壁滩上风很大,吹到脸上像刀割似的。戈壁荒漠上几乎看不到一棵树,就连草也少得可怜,贫瘠的土地上随处可见盐碱滩。夏天的太阳毒得能晒掉人几层皮。夜晚不光寂静而且寂寞,生活单调乏味。昼夜温差大得邪乎,经常能把人冻醒。刚到塔里木盆地,队员们水土不服,没听说哪个人没闹过肚子,没有十天半个月是适应不了的。
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荒芜苍茫,满眼黑色的砾石,满目死亡的沉寂。偶有几棵芨芨草或骆驼刺,灰蒙蒙地点缀着大戈壁的孤独和寂寞。只有萧萧的长风在狂啸,只有毒辣辣的日头在烘烤。
1979年9月20日,新疆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简称“新指”)在阿克苏召开地质工作会议,国家地质总局石油局、国家地质总局航测队、塔里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新疆地质局、新疆石油管理局等单位主要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会议,并特邀工业部佟成莅会。
会议由新指李奔指挥长主持,康玉柱代表塔里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作了题为《塔里木盆地石油地质特征及找油方向》的发言。康玉柱认为,塔里木盆地具有统一的前震旦系结晶变质基底、广泛的古生界基础和巨厚的中新生界盖层。该盆地是多构造体系控制的复合型盆地,对盆地起主导控制作用的是纬向系和西域系,具有多旋回、多成油组合特征,油质丰富,储集条件好,是形成大油气田的物质基础。圈闭类型多、可选择余地大,找油领域广泛,是我国重要的含油区。在对盆地生、储油条件分析中,对首次出寒武—奥陶系的碳酸盐岩生、储问题也应重视,注意在中央隆起寻找古生界的古潜山型油气藏。部署建议为着眼全盆,分区规划,加快普查,择优突破。
康玉柱建议,在工作部署上把油气勘探重点往塔北沙雅斜坡地区转移。理由是,根据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方法,研究认为,沙雅隆起在早古生代时可能西与柯坪隆起、东与库鲁克塔格隆起形成了一个东西向的沉隆带,航磁资料表明这是一个东西向展布的平静负磁场区,在晚古生代形成了隆起带。但沙雅隆起开始沉隆接受沉积。库鲁克塔格由太古界、元古生界和下古界组成,加里东末期运动使其褶断上升,大部分地区缺失上古生界及其以上地层。中段是库尔勒鼻状隆起,是库鲁克塔格向西倾覆部分。钻井和地震资料表明,鼻隆轴部为奥陶系,而上古生界和侏罗系仅分布在南北侧,第三系不整合其上,在加里东期与库鲁克塔格相连,在海西期被西域系改造而分割开来。西段是柯坪隆起,与库鲁克塔格十分相似。另外,柯坪隆起与柯吐尔、雅克拉潜伏隆起是同一东西带上性质类似的地质体。沙雅隆起上的柯吐尔、雅克拉、轮台隆起上的基岩埋深三四千米,在中生代仍处于隆起状态,于新生代形成北倾斜坡。所以,该隆起上不但有古生界,也应有中生界。在沙雅隆起上应注意寻找古生界、古潜山型油气田。基于上述认知,可知沙雅隆起油气前景较好,目的层埋藏浅,因此,提出了向这一地区转移的意见。会后,指挥部又向石油局领导作了汇报。
1979年10月,地质部在于湖南长沙召开的石油普查工作部署座谈会上提出:“塔里木盆地主要是先进行战略侦察。要着眼全盆,侧重塔北和麦盖提斜坡,继续在喀什坳陷进行工作,注意塔东坳陷区和巴楚隆起带的探索。要海陆并举、油气并重、新老地层并重。要充分利用物探手段,在一些重要部位打井。结合系统扎实的周边地面地质工作,加强综合研究,基本搞清大的构造格局、地层层序和生储盖组合,划分远景区,选准远景区,选准主攻方向,确定主攻战场。同时,要积极为上大钻作准备。”
根据地质、物探人员的建议,指挥部几度准备在塔东跃进1号重力高开展工作。1979年11月,在第三普查勘探指挥部(简称“三指”)召开的1980年工作部署会议上,预定了跃进1号重力高西高点跃进1井井位。
地质部石油海洋地质局对三指1980年油气勘查部署提出具体要求:“在着眼全盆地前提下,以塔北和塔东坳陷区为侧重点,在西起喀什、东到孔雀河、北起柯坪塔格、南以跃进1号重力高为南界的广大地区开展工作。”
塔里木的天就像孙悟空的脸,说变就变。
1979年,5012井队在喀参1井作业。腊月二十九,临时负责井队食堂的李德满到处找关系,整整忙活了一天,费了老大劲才从疏附县商业局采购到六箱啤酒。下午6点多,他和驾驶员开着老解放车往井队赶。冬季天短,没走多长时间天就黑了。不足100公里的路程,跑了四个多小时还没跑回井队,汽车在无路的戈壁滩上迷失了方向。第二天就是除夕,驾驶员急得心里发慌。李德满安慰驾驶员,别急,停车,咱们下去好好辨别一下方向再走。其实他心里比驾驶员还要着急。两个人在茫茫戈壁滩上折腾到半夜才摸索着回到营地。李德满对驾驶员说,奔波了一天太累了,休息吧。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德满觉得浑身透凉,被冻醒了。睁眼一瞅,头顶上大风呼啸,沙子直往眼睛里落。莫非自己在做梦?他转身嚯地坐起来,乖乖,原来帐篷没顶了。再一看,睡在身边的马福才不见了。他大声喊马福才的名字。马福才从外面跑进来说:“你睡得像死人一样。这场风暴得有九级。”
李德满赶紧穿衣下床,加入抢救帐篷的战斗。大伙一直忙碌到天亮,风暴才渐渐地平静下来。队员全都灰头土脸,像泥塑一样,都饥肠辘辘地等着开饭。李德满跑进伙房帐篷,顿时惊呆了。他日夜奔波呕心沥血为除夕会餐筹备的各种菜肴盆子东倒西歪,有的甚至撒了一地。他傻愣了半晌,无奈地蹲在地上呜呜地哭出声。
大伙听到哭声,跑进来一看,全都傻眼了。猪排、猪肘、手抓羊肉、鲤鱼、牛肚、卤鸡、肉丸子面目全非,全变成了形状诡异的沙土疙瘩。
“怎么搞的?不盖严实,这些年货还能吃吗?”
听到个别同志的议论,李德满哭得更伤心了,泪水将脸上的沙尘冲刷出两行泥痕。这位来自青海高原的又瘦又矮、皮肤黝黑的临时炊事员兼代理管理员,既委屈又自责。这是5012井队的弟兄们在新疆过的第一个年,想家的那份心本来就重,历来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李德满,为了给大伙筹备这些年货,自己跑到100多公里外的疏附县,求分管肉食公司的副县长批条子,才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采购到这些宝贵的食材。现在大家过不好年了,他怎能不愧疚、怎能不痛心疾首呢。
除夕当天,井队队长杜荣华和副队长王守忠站在李德满同志左右向工友们道歉。每人发两个馍、两瓶啤酒。大伙领了自己的那份年夜饭,全都转身离去悄悄地回到帐篷,几个人围着铁炉子或地炉子,一口馍一口啤酒,谁也不言语,闷闷地往下咽。大伙都不敢对视,谁都不愿提起在家时的除夕,生怕提起了,戳到痛心处会勾起一场火气,惹是生非。一普自1960年在山东组建,不会餐的除夕,这是第一次。
何明山进疆前把妻子送到乌兰县的哥哥那里,前几天收到妻子来信说,因年关将近,他哥又把她送回娘家了。妻子在信中说:“明山,你就看着我们娘儿仨流浪在湟源山沟?”想到自家妻儿居无定所,而地质队员们也是把家绑在腿肚子上,远走天涯,四海为家,哪里来的房子供妻儿们躲风避雨。何明山放下啤酒瓶,默默走出了帐篷。过了个把小时,还不见何明山回来,大家着急了,相继涌出帐篷,点上火把,打着手电,四处叫喊他的名字,却没有回音。队长让大家分头去找,最后发现何明山手里握着妻子的信,扑在沙丘上呜呜地哭泣。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见到这种情形,哪个铁石心肠的汉子能不掉泪?悲伤的情绪感染了大伙,许多七尺男儿也都跟着抽抽噎噎。
地质专家魏开谈说起当时的情况,一脸无奈。他说:“那时候地质工作真苦啊!地质队主要在野外作业,荒无人烟的沙漠中没有路,只能雇用骆驼驮运仪器设备,每到一条测线,物探队员只得背着重达十几公斤的设备深入塔里木河床开展工作。吃住都在野外,每天被漠风吹得像土人似的,走到哪儿睡到哪儿,早晨起来被子上一层沙土,没法整理,随便一卷就得了,我们把它称为‘卷席筒’。身上的灰土再多都没有办法清洗,经常一个多月洗不上一次澡。汗水被晒干了,在衣服上留下白色的汗碱,没有条件每天换洗衣服,衣服上就留下一股汗臭味。有人为我们地质工作者编写了打油诗:‘有女不嫁地质郎,成年累月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抱回一堆臭衣裳。’还有:‘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原来是搞勘探的。’说我们像‘逃难的’‘要饭的’,尽管有点过分,但很形象。”
还有一位同志说,他的女朋友就是嫌他的工作太艰苦,一年见不上几次面,和他分手了。
笔者问他:“你遗憾吗?”他平静地说:“没啥。当时接受不了,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也不能怪人家。哪个女人不想找一个能够长相厮守,能在家里照顾自己的男人。但我作为一名地质大学毕业生,我有我的理想,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要在这个行业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平淡地补充道:“我不需要别人的理解和认可。我没有豪言壮语,在我们这个单位,比我思想境界高的人多的是。我们当中有许多同志,父亲临终前都没有赶上送老人最后一程,别说尽孝了。所谓的尽孝就是每年给家里寄点钱。有些同志爱人生孩子也没法陪伴,等回到家里孩子早已出生了。要是顺利还好,遇到不测,哭也没用。”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眶湿润了。
多么可爱的同志啊!笔者听得鼻子都跟着发酸。
他们献给祖国的是满腔的热诚,是无私的爱,是自己的青春、生命、爱情和家庭。怎能不让笔者向他们表示敬意?只能说,心中有信仰,人生就豁达!
1979年底,国家地质总局新疆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第三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简称“三指”。
麦参1井在上石炭统灰岩中首次取得含油岩心,测井资料解释含油层可能有10层,在4150~4242米井段上部射孔1米后测试,日产天然气500立方米,从而证实石炭系碳酸盐岩是盆地的重要生储油岩之一。
地质部部长孙大光在现场视察工作时,对此给予充分肯定。这个时期共钻井4口,进尺16120米。但油气勘探工作也遇到了很多难题。
比如,巨厚的第三系“黄被子”问题。喀什坳陷内的上第三系厚度一般在四五千米,某些地段厚达七千米,基底埋深超过15000米。为解决模拟地震仪记录长度不够的问题,一物彭诚同志组织了有关技术人员对地震仪进行改装,以两圈录制方法,取得深层反射,为了解坳陷的地质、构造情况提供了依据。然而主要含油层系埋藏过深,当时的钻探能力不可及,造成了油气勘查部署上的困难。
再如,局部构造上下不吻合问题。在明尧勒背斜、木什背斜、喀什背斜等构造,地震浅层反射层与深层反射层的构造形态和位置有较大差异,而中层未得到可靠反射资料。钻探资料证实,地层破碎严重,产状甚陡,勘查工作难以顺利进行。
1980年初,石油局决定把工作重点逐步向塔北沙雅斜坡地区转移,三指将地震队、钻井队部署在该区进行勘探。
1980年9月6日,三指在乌鲁木齐延安宾馆召开塔里木盆地规划部署论证会,与会的石油海洋地质局和各地区石油局、队的专家反复讨论,原先提出的许多方案都因各种具体问题和困难被推翻。最后,大家提出将工区转移到塔北坳陷的建议。经过对资料的研究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库车坳陷以南、满加尔坳陷以北这一地区值得深摸。于是会议决定,将塔北作为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查的主攻战场是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