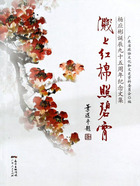
我的父亲与陶铸、赵紫阳同志
我的父亲在“文革”中和很多广东干部一样,头上都有一顶“陶赵死党”的帽子,父亲比别人还多了一顶“赵紫阳的军师、影子、灵魂”的帽子。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大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其中也包括所谓“陶赵死党”问题。习仲勋指出:陶铸、赵紫阳同志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期间,对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所谓“陶赵死党”之类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应当推倒。(中共党史出版社《习仲勋主政广东》189—190页)

1955年杨应彬和郑黎亚都在北京高级党校学习,这是他们在北京颐和园合影。
父亲先认识赵紫阳同志后认识陶铸同志。1950年12月,接华南分局通知,父亲从广东土改总团龙川分团副团长任上调到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任调研处处长兼方方同志政治秘书。方方时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兼土委会主任,副主任李坚真、陈冷。不久,1951年4月,赵紫阳从河南调来广东,任华南分局秘书长兼土委会副主任,而陶铸则是1951年底从广西调来广东,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从那时起,父亲就认识了这两位领导,并在他们身边工作了10多年。
赵紫阳同意父亲调到省委工作
1955年父亲在广东省人委办公厅主任位上到北京高级党校学习一年,毕业后,最初要他到《南方日报》去当副总编辑。因在党校学习时高度紧张患了失眠症,觉得自己不适应报社工作。于是父亲到省委找赵紫阳说:“在报社日夜工作我吃不消,我希望能调回地方工作。”赵紫阳同意父亲的意见,就把他调到省委任副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主任,从那以后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父亲一直在陶铸、赵紫阳领导下,从事农村工作整整10年。

陶铸十分关心清远洲心经验,曾多次到洲心蹲点调查。图为20世纪50年代陶铸在广东的干部试验田参加劳动。
实事求是使广东少饿死人
深入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说是陶铸、赵紫阳身上最闪光的特征。他们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广东的领导班子也风尘仆仆长年扎根基层。
父亲回忆说,赵紫阳作为主管农业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长期坚持一种习惯,他不喜欢让地委、县委的干部到广州来汇报工作,而是经常下乡,到下面去开会调研。他常常边走边看边调查,这样做往往能把问题看得更准,提出的措施往往更贴近地气,收到实效。父亲主要是协助陶赵分管农业,制定农业政策,因此也常常下乡,我们小时候很难见到父亲。难得有一个星期天全家团聚,如果父亲刚好在家的话,他一定会领着我们几兄弟到东湖划划船,或者到广州文化公园看看画展,那是我们最期盼的幸福时刻。
建国后的中国农村是政治运动的重灾区。从1953年全面完成土改后,毛主席企图通过迅速改变生产关系的做法来发展农业,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短短5年时间,中国农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一下子跨越新民主主义进入到已经接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正如当时盛行的一句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似乎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鼓足干劲”去“大跃进”,共产主义就不遥远了。于是乎全国很多地方都争先恐后地报高产、放高产卫星,特别是河南、湖北等省,以此来博得毛主席的欢心,证明人民公社的正确性。

这是大跃进年代粮食放高产卫星的宣传画。
1958年夏天,父亲随同赵紫阳到庐山参加中南局召开的农业会议,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见到赵紫阳就问:“早稻广东收割要早些,我们湖北已经收割了,你们产量怎么样?”赵告诉他说:“我们一亩水稻就上到380斤。”王任重说:“不可能!我们武昌地区已经解决了亩产5,000斤,现正在解决一万斤的问题。”赵紫阳听后很不以为然,王任重离开后,他对父亲说:“我们天天在南粤这块土地上摸爬滚打,现在这种耕作技术、种子和田间管理水平,不要说是上万斤,就是上千斤也很困难的。”赵紫阳决定不学湖北,还是按照广东的实际情况来做。庐山会议结束后,赵紫阳回到广州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在开会前给陶铸打电话说:“我们今年的晚稻,通过努力争取比早稻产量翻一番或者翻半番还是有把握的。”翻一番是760斤,翻半番是500斤,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然不久之后,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违背自然规律口号的鼓吹下,全国各地放出的亩产卫星一个比一个高,广西放到最大的卫星是亩产13万斤!而上头似乎又很欣赏这种浮夸吹牛的氛围。一直顶着,不愿讲假话去放高产卫星的赵紫阳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实在顶不住了,也不得不放了一个亩产6万斤的卫星。但他对父亲说,在报道时要说明这个卫星是怎样放出来的。于是在父亲的安排下,当天的《南方日报》,在一大群农民围着一块密密麻麻稻田边敲锣打鼓放卫星的照片下,有这么一段文字说明:这是在水稻收割前半个月,把60多亩的水稻移植到一亩地里去,为防止腐烂,还用了几部鼓风机日夜往里面送风。
接下来的三年(1960—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陶铸赵紫阳比较实事求是,没有乱放卫星,所以,广东饿死人比较少,大概是死了60多万人,相比四川、河南、安徽死了几百万人,广东还是相对稳定的。
父亲后来在总结这段时期的经验教训时,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件“惊人秘密”,庆幸自己没有因为头脑发热酿成后果。当时,父亲到曲江县樟市公社调查后,在家伏案两天,完成了《从一个公社看三个“并举”》(后改为《从滴水看太阳》)的调查报告,副标题是“广东省曲江县樟市人民公社是全面跃进的一面红旗”,并经省委上报中央。毛泽东主席看后颇为欣赏,一边看一边改。这篇短短五千余字的报告,毛主席亲笔对文字和标点符号的修改,竟达30余处,他准备加批注后作为典型发到全国宣传学习。父亲知道后,非但没有一丝的欣慰,心情反而十分沉重。在这篇报道中,对樟市公社的一些做法,父亲是加以肯定和宣扬的。但经过深入调查后,父亲发现有虚报造假成分,如果毛主席批转了这篇报道,一定会助长全国泛滥的浮夸风。于是,父亲找到陶铸,诚恳地向他作了检讨,并要求陶铸立即向毛主席报告说明:“樟市产量尚未核实,先不要转发”。这份虚假报告毛主席最终未用,并于1958年12月29日路经郑州时,不无懊恼地将他修改过的这份报道甩给了河南省委。1978年河南省委办公厅在收集毛主席手稿时,发现了他亲自修改过的这份档案材料,他们将原稿报送中央,并将复印件寄给了广东省委。我们听完这个故事后,一方面为父亲遵循陶夫子“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精神而肃然起敬;另一方面也为父亲“冒犯龙颜”、“欺君罔上”的举动感到后怕。

赵紫阳长年坚持在农村基层调研,图为20世纪60年代赵紫阳在电白县考察时合影。左一杨应彬,左四赵紫阳
毛主席批转赵紫阳杨应彬的反瞒产报告
这个时期导致大批农民饿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中央提出在农村实行高征购和反瞒产私分的错误政策。既然各地都大丰收放高产卫星了,而且是十倍、几十倍地丰收了,那么国家对农民征购指标也就大大提高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增产而是减产了,下面征收不上来,上面就认为是农民瞒产私分了。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领一支工作队到东莞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从农民的米缸里挖走了558万公斤粮食和1.2万元资金。与此同时,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当时叫雷南县)调查,父亲也去了,并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以赵紫阳、魏今非、杨应彬三人的名义报告省委,介绍了徐闻县反瞒产运动的经验。不知什么原因,陶铸的东莞经验只登载在《人民日报》上,而赵紫阳的经验却由中共中央批转了,毛主席还亲笔为中央起草按语:“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给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及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

这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杨应彬写的一个报告。毛主席后来未用把它甩给了河南省委。
广东反瞒产私分的运动虽然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肯定和表扬,但陶铸、赵紫阳不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他们一方面要紧跟中央,紧跟形势,但一旦发现问题后,就下决心纠正。就在徐闻经验出来后不久,1959年3、4月间,省委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召开专门会议,终于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么多。省委分析说,一是头脑发热,产量报高了。根据报产制定的征粮计划不符合实际,因而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公社饭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吃干饭”,“敞开肚皮吃饭”,造成大量浪费。为此,省委立即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不久,陶铸赵紫阳等人来到潮安,在群众大会上,陶铸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作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
在紧接着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父亲作为列席常委作了一次发言。他根据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出现这么严重失误的关键是在三个关系上没有掌握好:一是精神和物质关系上,过于强调精神的反作用,导致主观脱离了客观;二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上,过于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导致生产关系处于不断动荡的情况下,生产力又没有得到发展;三是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上,过于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此群众和基层干部思想不通时,就强调“拔白旗,插红旗”,强调“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导致揠苗助长的情况。
其实父亲这个发言完全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结合我省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一些教训而讲的。但在那年夏天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结束后,就被时任省委候补书记的张云看作是典型的彭德怀式的右倾言论,正式向省委提出要把杨应彬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陶铸听后马上说:“在我们身边工作的同志,他们的思想状况,我们是了解的,不要因为一次发言就乱戴帽子。”赵紫阳也说:“应彬同志的那个发言,我们都是赞同的,如果有错,那就大家一起承担。”陶铸赵紫阳头脑清醒,爱护干部,保护父亲逃过了一场劫难。
赵紫阳对“洲心经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恢复广东农业生产,解决全省人民的吃饭问题,赵紫阳敢于探索创新,采取灵活措施。1961年,父亲在下乡时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农民在公社化后迫于生计,都不把公家大田的耕种施肥放在心上,一心只顾自己的自留地或新开荒的土地上,结果公私两头都不增产。这时,清远县洲心公社干部发现,农民在插秧后到收割前有八九十天的时间,若管好水、用好肥对增产丰收能起到关键的作用。洲心经验就是在插秧后,生产队的干部及时对每块田进行估产,然后把这八九十天的管理权承包给农民精心耕作,如果增产了,那么就拿出其中一部分奖励给农民,农民当然高兴了,大田耕作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父亲到洲心公社详细调研后,把这种做法叫“联系产量承包责任制”,但在总结时又怕被扣上“包产到户”的帽子,有违中央精神,于是给它戴了一顶“十统一”的帽子(统一计划、犁耙、播种、插秧、收割、打场、晒谷、过称、保管、分配),叫“十统一的田间管理超产奖励责任制”。虽然十分拗口,又诸多限制,但对恢复广东的农业生产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陶铸、赵紫阳也都深入洲心公社去蹲点调查,赞成这个做法,让父亲写好方案后就在全省每个县先搞一个公社铺开试点。

这是2015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洲心经验》。
但是好景不长。1962年7、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赵紫阳让父亲携带责任制文件一起到了北戴河向中央汇报。由陶铸先送给刘少奇,他立即表示同意,再送毛泽东,他却不表态。因为这时毛主席心里酝酿着一个更大的政治运动,对这些解决吃饭问题的方案根本不感兴趣。在这个会议快结束前,毛主席又作了一个形势、阶级、阶级斗争的报告,提出了后来导致“十年浩劫”的著名论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陶铸一看风向逆转、政治气候不对,就对赵紫阳说:“赶快把试点范围缩小,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公社。”赵紫阳打电话回省里,传达了陶铸指示精神。当赵紫阳回到广东后,发现原来一个县搞一个公社试点的做法没有变,有的还越搞越多,很多公社都效法洲心经验做了起来。他觉得这个办法能解决农业生产、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群众和干部都愿意去做,也就采取“睁只眼闭只眼”,乐见其成了。后来,江西省委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反映江西干部跑到广东清远去参观,看到洲心经验还在实行,回到江西就争论起来了,有的认为好,有的认为是包产到户,争执不下,于是就写信到国务院去问,这样做行不行?是不是单干?当时罗瑞卿副总理在值夜班,收到这个反映后就打电话问广东。接电话的刚好是父亲,他回答说还在小范围做试点,就搪塞过去了。

收录在《洲心经验》中的这个文件,反映了广东省委大力支持积极推行洲心经验的决心。
赵紫阳偷换“四清”标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1964年,全国农村又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的“小四清运动”。赵紫阳紧跟中央和陶铸的部署,在运动之初也是积极投入的。广东省委还邀请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来广东作报告,介绍她的“桃园经验”。
父亲也随赵紫阳一起来到中山县附城公社库充大队蹲点。由于毛主席把中国广大农村看成是滋生资本主义的重灾区,因此在建国十多年后,“四清”工作队到农村去,仍然采取当年在国统区的做法,隐姓埋名,秘密串联。赵紫阳化名“赵明”,父亲化名“杨山”,同住在一座碉楼里。他们同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村子里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调查村干部的经济状况,看有没有多吃多占的现象,把对敌斗争的整套做法又搬到了广大的农村。
赵紫阳和父亲在此期间,逐渐认识到“四清”运动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伤害,于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补救,实事求是帮助农民兄弟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对当地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问题进行批判后,在退赔时还把他家里的自行车没收了。农民就反映,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村,自行车是一件基本的生产工具,运种子、肥料都靠它,把自行车没收了,叫农民干部怎样搞生产?赵紫阳了解这个情况后,就让四清工作队把收缴上来的自行车退还给农民干部。
赵紫阳一方面要忠实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一方面却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他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他后来在南海县大沥公社搞“大四清”中就大胆地提出两条检验“四清”运动的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了没有?粮食和多种经营增产了没有?二是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人均收入到达200元。他搞“四清”运动的标准不是什么“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而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这在当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广东在“文革”前的1964、65、66年连续三年增产丰收,物资丰富、人民相对安居乐业。
“文革”使赵紫阳大彻大悟
“文革”中,赵紫阳作为广东头号“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早就被打倒了,父亲作为“陶赵死党”,加上“反共教育家陶行知的徒子徒孙”、“大军阀张发奎的亲信”、“特支成员是叛徒特务”等罪名也被打倒了。父亲多次陪同赵紫阳和许多领导干部一道,被拉到越秀山批斗,炎炎夏日在广州马路上游街示众。在越秀山批斗会上,造反派高呼:“火烧赵紫阳!”赵跟着举手喊:“火烧赵紫阳!”;造反派高呼:“打倒赵紫阳!”他不举手也不喊。造反派质问他,赵紫阳回答说:“我有缺点错误,你们要火烧一下,当然可以。但中央没有给我定性,你们要打倒我,我是不同意的。”
后来周总理指示广州军区领导把赵紫阳和父亲等二三百名中南局和省市领导干部都集中在警备司令部关押,客观上起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作用。赵紫阳后来又被转到湖南,1971年获得“解放”到内蒙古工作了一年,1972年回到广东工作。1973年父亲也从花坪五七干校回来了,并重新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父亲在这段期间,在不同场合多次听到赵紫阳讲到“文革”的教训,他说:“‘文化大革命’使我大彻大悟,今后不能再整人了。”他对原来整过他的人和专案人员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还请专案人员吃过饭。
父亲在赵紫阳身边工作了12年,他对这位领导人为人正派、有魄力、善于思考、深入实际、作风民主、生活朴素的崇高品质和作风十分敬仰怀念。有一次父亲和他一块到汕头,因爷爷奶奶想吃客家的糕粄,让父亲买些薯粉带回去。赵紫阳发现车上有一包东西,以为是谁送来的,很严肃地问为什么要拿这东西?父亲解释说,是他自己买的,不是别人送的,赵紫阳才没有追问下去。他对子女的管教也是很严格的,他们家吃饭时都不吃水果,生活上艰苦朴素。
赵紫阳也是一位尊重下面干部、倾听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人。1962年暑假,我们曾有机会陪同赵紫阳和父亲一块到肇庆七星岩和鼎湖游玩。大人们忙于开会,会后父亲留在住地赶写报告,赵紫阳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爬鼎湖山。大半天后,在下山途中,父亲写完报告赶过来与我们汇合。这时候,看着父亲被熬红的双眼,赵紫阳动情地对他说:“看来我们赵家真的对不起你们杨家啊!”我们当时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文革”后,我就此事问父亲。他说:“当时赵是有点飘飘然,虽是一句玩笑话,我当面就批评他,此话不妥,他也谦虚地接受了”。赵紫阳是用赵氏的北宋皇帝与精忠报国的杨家将的关系与父亲开了一玩笑,没料到到“文革”中竟成为他“有野心,想当皇帝”的一条罪状。
赵紫阳对“永生难忘”的恩师陶铸也是一分为二的。1979年是陶铸逝世10周年祭,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为缅怀这位恩师,特意把父亲请到四川,帮他写了一篇纪念陶铸的文章《一位卓越的共产党人——怀念陶铸同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赵紫阳并不隐讳这位伟人的不足之处,他和父亲在讨论怎样全面评价陶铸时说,陶是大刀阔斧,能够很快打开局面的帅才,但他的不足之处是没能再深入下去,有些事情就不仔细了,就没能办好了。父亲根据赵的这个观点,在文章中也把这个意思写了进去。
1981年9月,广东党史部门约请赵紫阳为陈郁老省长写篇纪念文章,此时赵已调到北京出任国务院总理,工作繁忙,身边的同志对陈老都不熟悉。于是他给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父亲写了一封信,想请父亲代劳。他在信中提出写陈老的两点意见,“一是老人家精神高尚,确是一位高尚的人;二是满腔热情,对党对人民对同志都是热心肠。希望着重从这方面写。”赵紫阳在信的末尾十分谦虚地询问父亲:“不知你有无困难,可否答应?如同意,你可先考虑,写出个稿子来,待我有时间(恐到11月初了),再共同研究修改。”赵紫阳尊重下属、倾听下面干部意见的民主作风,也让下面的干部敢于向他提意见,甚至是批评意见。1982年10月22日,父亲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指出他在驻外使馆政工会议上的讲话第三部分有一处应“在文字上增加几句,以免引起误会”。一个省委秘书长敢直接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提出不同意见,这是老一辈革命家之间普遍的革命传统。
赵紫阳对忠诚实干,敢于担当,思维敏捷,逻辑严谨,才华横溢的父亲是十分欣赏和器重的,对他不计名位,一心为公的高尚品德也是十分敬佩的。据“文革”中省委机关大字报披露,1966年以前赵紫阳百分之九十的报告、文章都是出自父亲之手,这也是“赵紫阳军师、灵魂、影子”那顶帽子的来源。父亲曾多次向陶铸、赵紫阳提出,长期在机关工作容易脱离实际,希望到下面地市做实际工作。陶赵当时都爽快地答应了,但就是不放人,总是安慰父亲说再等等吧,这样一拖就是10年。父亲从1956年到省委任副秘书长,除去“文革”间断了几年,在此位上整整坐了20多年,直到1978年才任省委秘书长。出于对父亲的了解和信任,赵紫阳到北京当上总理和总书记后,都曾有意调父亲到北京,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要职,协助他工作。父亲这时已届花甲之年,虽有丰富的斗争阅历和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但他一生淡薄功名,因此他向赵紫阳表示“力不从心”,没有赴任。

20世纪60年代,杨应彬陪同赵紫阳视察合影。左三杨应彬,左五赵紫阳
2015年7月13日父亲逝世后,一些朋友在和我们一起悼念父亲时提了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假如当年你父亲同意到赵紫阳身边工作,那么,后来的事情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只能一笑答之:“历史没有假如,人生亦不可能重来。我看还是这样好。毕竟父亲幸福地活到了习近平时代,安详地活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他知足了,也能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