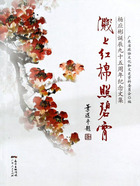
我的父亲与习仲勋、任仲夷同志
1978年初父亲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同年4月,已经离开工作岗位16年,刚刚恢复组织生活的西北汉子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接替已经上调北京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主政广东。(1978年11月,习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到广州的第二天,习仲勋出席了广东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的第一次讲话,言语不多,但感情真挚、朴实无华,他说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广东,要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实事也证明,习仲勋同志虽然主政广东只有两年多时间,但他殚精竭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忘我工作,他不仅带领省委、省政府一班人齐心协力,团结战斗,领导广东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杀出一条血路”,开创了广东工作的新局面,而且为全国改革开放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父亲有幸作为班子成员,全力勷赞习仲勋大刀阔斧实行农工商业的改革,创办特区,留下来难忘的“我们在广东省委共同工作的日日夜夜”(习仲勋给杨应彬信件的话)。

1978年春节,杨应彬陪同习仲勋在广州看花市。左一杨应彬,右一习仲勋。
我深切地感受到,父亲对习仲勋、杨尚昆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十分敬佩的,为了改变广东的落后面貌,为了老百姓的丰衣足食,他拼尽了全力和全部才智,协助省委主要领导进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探索和实施。那阵子,父亲既要陪同习仲勋下乡调查、开会写报告,协调常委会的日常工作,还要陪同杨尚昆熟悉广东省、广州市的情况,忙得无法分身。有一次吃饭时,父亲轮流接听两位领导的电话,饭菜都凉了。我见状讲了一句牢骚话:“爸爸现在成了一仆二主了。”父亲听后很不高兴,严肃地批评了我。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改革开放重任千头万绪,过去体制留下来的桎梏积重难返,没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是寸步难行的。以至一次父亲骑自行车上班时不幸摔了一跤骨折了,不能上班,只好躺在床上批改文件。杨尚昆有事找父亲,径直跑到家里来,顺手抓了一张小竹椅,坐在父亲床头一聊就是大半天。
“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特区”等等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绝不是哪位“设计师”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习仲勋心里装着老百姓,在处理广东边境大规模偷渡逃港潮的实践中,向中央“讨”回来的。父亲在《金华集》回忆录说道:“在新的历史时期,广东最大的创举是在改革开放中设立特区。问题的提出,首先是50年代后期以来在广东边境上出现了经济衰退,人员外流的严重现象。广东和港澳山水相连,土地接壤,而且港澳80—90 %是广东人,在新界种蔬菜的是宝安人,为什么他们那边繁荣,而我们这边却是萧条?”“因此省里的领导同志就想,假如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我们会发展得快一些。外流问题也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于是1978年冬,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希望中央给广东更大的支持,给地方以更多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的资金;同时在临近香港地区搞拆船工业,以解决钢材问题;希望中央允许在来料加工这些经济事务的处理上给广东处理权。”习仲勋代表省委提出的要求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后来邓小平进一步要求广东大胆试验,创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决定: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四个地区为特区,拉开广东改革开放的序幕。父亲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曾填“如梦令·开拓者”一阕:“天地何时开凿?历史如何写作?人类在思维,又是如何探索?开拓,开拓,天际朝阳喷薄。”盛赞以习仲勋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勇于开拓的大无畏精神。

杨应彬代表省委起草的这份报告,获得中央的肯定和支持,换来了中央50号文件,揭开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序幕。
广东农村自发地尝试推广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是比较早的,也是比较大胆的。农村基层偷偷实施“产量责任制”,但谁也不敢公开说。习仲勋来广东后,首先把农村体制改革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一次他去从化调查回来,顾不上休息,吃过晚饭就把父亲和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找去。他说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正在试验“产量承包责任制”,效果很好,问他们是否可以推广?父亲说,这种做法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广东推行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的继续和发展,接着父亲就把上世纪六十年初,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渡过“经济困难”时期,清远创造了“联系单位产量责任制”的“洲心经验”的过程和历史遭遇说了一遍。习仲勋听完后,沉思了一会说:“我看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态度异常坚决,表现出习仲勋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坚定性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在习仲勋的大力推动下,形成了“中间不动,两头包”(即广东中部较富裕的农村不动,粤东、粤西较贫困的农村先动)的情况,但没过一两年,中部地区也推广这种做法,于是全省都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东农村很快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较好形势。
无独有偶,工业体制的改革最早也出现在清远县。在时任韶关地委马一品书记、张正甫副书记的支持下,从1978年开始,清远县部分企业试验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收到了良好效果,此举得到习仲勋的肯定和支持,然而“倒春寒”很快就吹来了——1979年5月,省财政和劳动部门联合发文要清远县停止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反对者的理由堂而皇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清远县的做法无疑是把应上缴国库的钱“截流”了,违反了国家财经制度和纪律。
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省里领导出席了1979年8月在广州召开的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认真听取了双方激烈的辩论意见。习仲勋在最后发言时强调:“一定要解放思想,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的规定,如果实践证明不对,也可以经过一定的手续改过来,不要不敢越雷池一步”。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在工业战线,一定要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一课。”会后,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由各地选择若干县的工业企业,仿照清远县的办法和本次大会讨论提出的改进意见搞试点。
但清远县的经验却因为有分歧,看法不一致,在广东的推广受到较大阻力。习仲勋知道这个情况后很生气,他说:“开会的报告、总结,丢掉了清远的经验,我一听到这点我就很有意见,这就不大对头。去年8月才决定的,才过了10个月,经验你也不总结了,你又偷偷摸摸的把它去掉不提了,老实说,大家有点生气。”1980年7月5日,习仲勋为此决定到清远县调研,陪同前往的有父亲和省经委主任王焕等人。习仲勋深入清远县工业企业调研,召开县部委办局领导和公社(镇场)党委书记座谈会,他说:“清远经验就是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我看你们这条路子很对,就是把经济搞活!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加以改正,不合理的体制加以改正,把人的手脚解放开来!”父亲目睹习仲勋一切从实践出发,一切为群众着想的大无畏精神和举措深受感动,当场赋诗一首:“经验原从实践来,还凭妙手匠心栽。长征路上辟新径,带起群芳处处开。”记下了广东改革开放艰苦历程中值得追忆的一幕。

杨应彬陪同习仲勋、杨尚昆考察,左一杨尚昆,中习仲勋,习后杨应彬,右一任仲夷。
习仲勋于1980年11月调离广东后,对曾经与他共同工作过的战友、同志是十分关心、耿耿于怀的。1997年,父亲应中央党史出版社之约,写了一篇“回忆习仲勋同志在广东的二三事”,习仲勋立即于当年9月18日给父亲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看到你写的 ‘回忆习仲勋同志在广东的二三事’后,使我回想起我们在广东省委共同工作的日日夜夜。你的真实性文笔,把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种种矛盾,和我们呕心沥血为人民的丰衣足食而进行的拨乱反正,以及为广东经济腾飞打下坚实基础的许多事情跃然纸上。衷心感谢你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在北京逝世。父亲和母亲联名给齐心大姐发去唁电:“仲勋同志是我党我国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革命战争年代,驰骋西北,建国后勷赞中央,都作出巨大贡献,在 ‘左’倾路线压制下,曾受到长期不公正待遇。一旦雨过天晴,又焕发出青春,为新时期的改革和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主持广东党政工作,带领全省干部和人民,锐意开放改革,使广东始终站在第一线上,为全国带了好头。我们在仲勋同志和省委领导下工作,体会是极深的。广东和全国人民,将永远牢记他,把他的光辉榜样作为继续前进的动力!”

1998年冬,杨应彬、郑黎亚到深圳迎宾馆看望习仲勋、齐心夫妇。
讲广东的改革开放,不能不讲任仲夷。1980年底,任仲夷从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南下广东,接替上调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主政广东。在任仲夷任省委第一书记的4年多时间,父亲一直是常委,前三年兼任秘书长,后两年分管宣传文教工作,与任仲夷有很多接触。父亲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给我的印象,任仲夷同志是一位大兄长,是我们省委领导班子的好班长。在岗位上时,他发表了许多精彩的观点,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起着思想指导的重要作用,使广东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即使退下来后,他也经常发表一些好的意见,使人耳目一新。”
任仲夷到位伊始,正是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遇到重大危机的关口。一方面,深圳珠海特区拔地而起,短短几年时间,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就以“深圳速度”展现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随着特区建设的深入发展,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如特区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关系问题;派购缩小了,议价扩大了;基建战线拉长了;高价收购的东西多了,转为出口的农副产品多了;外汇收入多了,但外汇又不用来购买国内所需的生产资料,而是进口高收消费品,冲击了国内市场等等,这些负面效应最突出的是沿海走私贩私活动更加严重,一些不是特区的地方也有走私贩私活动。后来有一位记者在《经济日报》上撰文,说“广东改革开放十年,全国议论十年”,“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这种议论在头几年尤甚。广东按照中央的指示,实行改革开放,创办经济特区,有人就说你是在搞香港化,搞资本主义化,是在搞租界,出卖主权;广东先富起来了,有人就说“广东是赚了内地的钱”、“广东变特区,我们变灾区”、“广东除了国旗还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有些甚至还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任仲夷
广东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同时也引起对改革开放持否定意见的部分中央领导的议论和非议。中央书记处于1982年1月11日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胡耀邦总书记又于2月11日至13日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这次会议气氛极其严肃,不像以前那样轻松活泼。弟弟小杨回忆说,去开会前就感觉父亲承受巨大压力,以为这次父亲上京可能就回不来了。会上发了好几份反走私的文件,特别是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一份《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十分耐人寻味。因为对开放政策和创办特区,一直存在争议,其中有一个论点,就是把特区和旧中国的租界相提并论,甚至划画等号。可见当时广东的领导班子承受着多大的责难和压力。座谈会结束后没几天,中央领导胡耀邦、赵紫阳又把任仲夷、刘田夫叫去北京,研究反击走私问题。后来,广东干部把这两次进京戏称为“二进宫”。“二进宫”原本是京剧的一个剧目,把它说成“二进宫”,与剧的内容毫无关系,只是借用这个词暗喻两次进京广东都挨了中央的批评。

杨应彬陪同任仲夷考察大亚湾核电站工地。
2003年夏,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5周年,中央和地方的传媒都组织撰写纪念文章。许多大媒体找到了已经离休多年的任仲夷,他一概谢绝了。《百年潮》杂志由总编带队来到广州,向任仲夷发出采访邀请,同样吃了“闭门羹”。刚巧我的一位好友张星沂的夫人是该杂志社的办公室主任,她通过我的关系邀请父亲同意接受采访。不料此事被任仲夷知道了,在采访前一天,他主动提出:“既然杨老同意采访,那我就当仁不让了。”于是,在珠岛宾馆会议楼二楼的一间会议室,我陪着父亲和任老,参加了采访活动。
确实,父亲只是一进宫,那是任仲夷率省委全体常委一块进的京。第二次进京,也就只有任仲夷、刘田夫两人,当时找任、刘二人谈话的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和时任总理的赵紫阳。而这4个人中,胡耀邦、刘田夫已经去世,赵紫阳失去自由,不能讲话,当时谈了些什么,怎么谈的,这次进京对广东的开放改革有什么影响?任仲夷不说,恐怕这段历史也就永远湮没了。
那天,任老情绪很高,虽然在开场白中,他不无幽默地说自己的话“可能是杂音,与当前的主旋律不合拍”,因此对采访一律不予接受。但话匣子一打开,他谈锋颇健,便滔滔不绝地说了三个小时,成了采访的主角,父亲只是在一旁作些补充而已。当时我就想,父亲主动接受采访的原因也是想“抛砖引玉”,看来的他目的是达到了。后来这篇访谈的内容经卢荻整理后以《伟人的胆识和胸怀——记任仲夷回忆邓小平》为题发表在2008年的《百年潮》杂志上,主要内容是谈到第二次进京时,中央领导人为了不使刚刚兴起的广东改革开放的事业夭折,如何苦口婆心地帮助任仲夷渡过难关,甚至细致到任仲夷向中央的检讨怎样写,都亲自交代,一再叮嘱。保任仲夷过关,就是保住了广东的改革开放。对胡耀邦、赵紫阳的用心良苦,聪明之极的任仲夷心领神会,他向中央写了一份自参加革命以来唯一的一次违心的自我检查,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个人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任仲夷理论深厚、思想深刻、胆识卓越、性格幽默、语言生动,他在历史大转折关头,为广东的改革开放立下开拓之功。200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仲夷论丛》,父亲阅后,撰写了“《论丛》精辟论点闪烁着20世纪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真理火花”一文,刊登在《当代广东》2001年第一期上。父亲在文中写到:“回顾20世纪,称得上比较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大体上有四次:第一次是20世纪初,孙中山同盟会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的论战,这是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民主共和思想的一次发扬、传播,对辛亥革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二次是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转播,弘扬民主与科学,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同“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直到延安整风运动取得巨大成果,对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和贯彻,起了很伟大的作用,使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缔造了新中国。第四次是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以来至今,这20多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仅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重大问题,而且回过头来反思了建国以来及至建党以来许多问题,特别是对‘左’的思想问题。这几次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都闪烁着许许多多的真理火花、思想亮点,照亮了许多人的眼睛。”

1999年国庆50周年,杨应彬、郑黎亚与任仲夷、王玄夫妇在北京新疆饭店合影。
父亲笔锋一转,明确地指出:“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仲夷论丛》这三卷书中许多精辟论点,就是一些火花和亮点,是在这第四次重大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的一个很好的典型。”父亲提出,任老的这三卷书中都贯串着一根红线,就是实事求是。《任仲夷论丛》是实事求是的反映,把这种实事求是精神,带到21世纪,必然会对今后工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8年11月7日,任仲夷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在前进中产生的,必须坚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去解决,绝不可走回头路,走回头路是没有任何出路的,而且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从这段话中,我们仿佛听到了几年后邓小平南方讲话中铿锵有力的警示语,也仿佛看到20多年后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上继续深化改革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