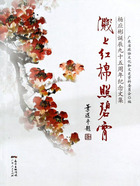
绚丽诗章奏响改革开放的最强音——在《杨应彬诗词》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各位领导、各位老同志、各位嘉宾: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在风景秀丽的东湖旁,出席广东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传承诗词艺术暨——《杨应彬诗词》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原本定在去年6月份召开,由于当时父亲病危,正在抢救中,学会领导建议推迟。去年7月13日,父亲与世长辞,我们失去了可亲可敬的爸爸,广东的诗词界失去了一位矢志发展繁荣岭南诗坛的忠诚战士和诗人。父亲生前曾多次婉拒为他的作品召开研讨会,唯独这一次。去年,我把准备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稿送给父亲审阅,他认真阅读并稍作修改后,于2015年4月28日在稿件上批示“同意”。
今天,这么多老同志、诗词界的这么多专家以及亲朋好友聚会一堂,对父亲的诗词开展研讨,我谨代表全家人,对大力支持出版《杨应彬诗词》和召开研讨会的省委宣传部、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及主办方——广东中华诗词学会表示衷心感谢!对出席研讨会的各位老同志、各位领导和诗词界的朋友、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我们家在东湖边生活了60年,父亲的三本诗集《东湖诗草》、《东山浅唱》、《东廓吟鞭》都是以东山、东湖命名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杨应彬诗词》研讨会,也是对父亲最好的缅怀和纪念。苏俊先生在父亲逝世后,撰一挽联,情深意切,十分感人,上联是“忽接骑箕讯,灯前落泪频。去为天上雨,来润岭南春”,下联是“勋业丹青在,文章道义亲。东湖今夜月,耿耿待何人?”我想,父亲的去世,固然是岭南诗坛的巨大损失,但是通过这次研讨会,一定能激发岭南诗界的各位贤能,化悲痛为力量,以杨应彬同志为榜样,在弘扬中华文化,传承诗词艺术的道路上奋发前行,为繁荣岭南诗词,传播正能量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所谓“东湖今夜月,耿耿照来人”。
我曾问过父亲:“您在上世纪60年代初写作了数十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为什么后来不写了,而改为写诗填词呢?”父亲回答说:“那些散文是我利用治病疗养的空闲时间作为练笔写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工作更忙了,时间更不够用了。只好在上山下乡时,或者是在国内外出差开会途中,或者有什么感触时,即景即事吟成草就的 ‘急就章’,有时候诗绪来了,一天可吟出三、四首,比写散文快捷多了。”于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父亲就与诗词——这种中华文学艺术的特有形式结下了不解之缘,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爱戴。上世纪80年代,花城出版社曾出版过父亲的两本诗集《东湖诗草》和《东山浅唱》,上世纪90年代中,父亲又挑选了部分诗词,由母亲郑黎亚用小楷誊写线装本《东廓吟鞭》。这三本诗集的书名“东湖”、“东山”、“东廓”都表明诗词创作的地点,共收录了父亲写作发表的诗词约700余首。2010年,大埔百侯中学校友会和肖如川、张云开等同志发起《杨应彬诗词》书画作品选的活动,动员了国内外300多位书画家用父亲的诗词写画作书,并在父亲九十寿辰时,在广东省博物馆以及梅州、大埔、深圳等地成功举办了《杨应彬诗词》书画作品选展览,为弘扬中华传统诗词文化艺术作出了贡献。
这次活动后,我萌发了整理出版一本比较完整、系统的父亲诗词集的念头,在征得父亲同意后,通过李绮文同志报告广东中华诗词学会,我的这个想法与学会领导不谋而合,他们对此事高度重视,并向省委宣传部作出报告,获得宣传部的支持,拨出经费出版诗集和举办研讨会。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收集了近千首诗词的《杨应彬诗词》终于在2014年10月付梓出版了。最近,在整理父亲遗物中,我们又找到二百多首未发表过的诗词,准备在这次研讨会专集或稍后出版的《杨应彬纪念文集》中收录出版,敬贻亲友共赏。
我对格律诗词没有研究,在座的很多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我不敢班门弄斧,只是略谈一下我对父亲诗词的一点粗浅认识,和大家一起共同来学习、提高。我读父亲的诗词总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父亲对事、对人、对景、对物用格律诗词的那种表述,我也是那样想、那样看,可自己就是写不出来;即使写出来了,也没有父亲的那种情真意切;有一定深度时,又没有父亲遣词用字的那种巧夺天工;在遣词用字上反复推敲了,又没有父亲诗词让人读起来的那种铿锵有力、朗朗上口;硬是拼凑一首朗朗上口的诗句后,还是没有父亲诗词的那种立意高新,让人回味无穷的韵味。
这些年在对父亲诗词的整理和编辑过程中,我试图挖掘概括这些诗词的特征,但由于水平太低而无法完成。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父亲的诗词就像一坛陈年的佳酿,愈久弥香。不论时光过去多久,今天当你咏诵起来,都依然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父亲的诗词写得那么美,那么感人,正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对为之而奋斗一生的理想和信仰一往情深,矢志不渝的结果。
早在1962年,父亲在一个座谈会上作了题为《更强烈的节奏,更激越的音调》的发言,便说生活绚丽多姿,题材不可能只有一种或几种,但是“任何时代都有个主旋律”,“有志于为人民大众而创作的作者”,“不论通过哪种手法,都得注入自己全副心力,力求作品与时代同脉搏、共呼吸、同主旋律合拍”。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实践的。
父亲诗词的创作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这段特殊的、火红的30年。他把壮年和晚年的全部时间和心血,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一个在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的斗争经验、以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丰富阅历,以洞察秋毫的政治敏锐性,同时又能娴熟地使用诗词这种特有的艺术形式,紧贴地气,抒发革命豪情。他的诗词作品都反映了与大众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具有强烈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今天读来仍然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和现实主义。
70年代末80年代初,解放思想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国策的必要前提,父亲为《开拓者》杂志创刊写下了《如梦令·开拓者》:“天地何时开凿?历史如何写作?人类在思维,又是如何探索?开拓、开拓,天际朝阳喷薄。”指出解放思想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原动力。
1979年秋,国画大师关山月以王维“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诗意写画赠送给父亲,父亲认真观赏《山雨图》后,揣摩到关老作画的动机,于是填《临江仙》一阕回报关老:
“木叶枯黄岩角黯,惟余涧底涓涓。忽闻雷震起西天。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久旱快哉逢大霈,顿时青满田园。蛙声啯啯兆丰年。大师三五笔,生意已盎然。”
“木叶枯黄岩角黯”,写的是大旱之年的自然景象,也是十年浩劫后国败民衰的真实写照;“忽闻雷震起西天”,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因而才有“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的壮丽景观;父亲巧妙地把王维诗句镶嵌于此,不仅符合词牌的韵律,也更突出了主题,凸显诗人技艺的精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决策符合国情顺应民心,就像是“久旱快哉逢大霈,顿时青满田园”;“蛙声啯啯兆丰年”,讲的是农业生产的大丰收,也是预示广东的文化艺术界即将迎来硕果累累的美好前景;“大师三五笔,生意已盎然”,既是颂扬关山月高超的笔墨技巧,也是对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央决策者的赞赏。关老的《山雨图》画得好,画得生动传神,父亲的《临江仙》词填得也妙,妙在画龙点睛。二者结合起来,便产生情景相融、珠联璧合的效果,起到激发人民紧跟时代步伐投身改革大潮的积极作用。
1980年7月,父亲和张汉青等同志陪同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到清远县调研,仲勋同志深入群众调查分析,充分肯定清远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改革之经验,认为应予推广。父亲十分赞成习书记的决策,即席赋诗一首:“经验原从实践来,还凭妙手匠心栽。长征路上辟新径,带起群芳处处开。”记录下广东改革开放征程中值得追忆和赞颂的一幕。
在改革开放决策受到质疑,有人挑起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时,父亲在众多诗词中鲜明地表述了支持改革开放的坚定立场,在《望海潮》中他写到:“神州一片光明,遍天南地北,东海昆仑。风暖送馨,花芳接露,欣欣万木争荣。金鼓震天鸣,奋激昂斗志,无畏精神。极目前程锦绣,策马又长征”。在《浣溪沙》中写到:“历史大潮难逆转,珠峰绝顶可登攀。诗人鼓吹再攻关。”在《好事近》中写到:“问国事如何?早已运筹帷幄。经济年年高涨,赖英明韬略。”
当父亲看到由于没有从严治党,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风气受到侵蚀,贪污腐化现象丛生时,严于律己、疾恶如仇的他忧党忧国忧民,用辛辣的笔锋针砭时弊,在《访北海》诗中他写道:“世道澄明吏不贪,海云深处浦珠还。生灵尚解是非意,不信人间廉政难。”在《感事》中写道:“风气颓然究可伤,十年浩劫更荒唐。会当斫取昆山玉,再塑雷锋黄继光。”在《过木棉庵》咏道:“人民自有春秋笔,奸佞从无好下场。”在《市桥赞》中他大声疾呼:“江山自是人民主,乜物当年李朗鸡!”在父母结婚五十周年之际,父亲深情地写下这样自勉的诗句:“秋光明艳照秋云,风雨同舟五十春。检点平生无大过,喜留清气度金婚。”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情操。
2002年4月习仲勋同志去世,父亲除了撰写纪念文章怀念这位对广东人民充满感情,带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显著成绩的老领导外,还深情地写作一首七律《怀念仲勋同志》,诗中最后两句充满激情:“江山代有雄才出,执掌征帆破浪开。”有不少朋友在读到这首诗后对我说:“令尊真是有先见之明,当时习近平同志还在浙江任省委书记,你父亲就能预见他将成为中国执掌征帆的领袖人物。”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巧合而已。但从中不难看出父亲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与怀念之情,也是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寄予厚望和鞭策。
父亲为弘扬中华文化瑰宝——中国当代诗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也身体力行创作了一千多首人民大众喜爱的格律诗词。他的许多诗篇,如《吟红棉》、《越秀层楼》、《忆江南·羊城好》、《减字木兰花·昆仑雪》、《踏莎行·萝岗香雪》、《临江仙·关山月 山雨图》等,都成为我省人民争相咏诵的佳作,成为团结和教育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而且超越国界,影响着东南亚华人社会。他的诗词被谱成曲子,如《羊城好》(傅庚辰曲)、《尽是故乡情》(朱松英、曾新芳曲)、《新兵抒情》(郑秋枫曲)、《春山春水》(曹光平曲)等,在广东音乐会上唱响;他的诗词被国内外数百名著名书画家争相泼墨书写,有十多首还被刻成石碑,竖立于祖国各地。他也因此被许多行家誉为“大诗家”、“诗宗”(程十发语)、“词人”、“道长”(赖少其语)。在赞誉面前父亲永远谦卑,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的:“我本南国花畔草,因风吹上木棉枝。”他满腔热情地鼓励更多年轻人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掌握古典诗词的规律,为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父亲曾在《东湖诗草》后记中的结尾时这样写道:“我的这些粗糙的习作,只不过是园角里的一株小草,最多也是点缀些春色而已。但是,小草尚且在文艺百花园中萌生了,那些能占尽春光的奇花异卉不就将大量开放了吗?”
父亲去世前和去世后,人们对他评价时讲得最多的两句话是“德高望重”、“高风亮节”。我们今天召开这个研讨会,我想首先要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就是诗词界常常提到的“诗心”。一个没有理想和信仰,没有对祖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和生活充满热爱激情的人,纵使他的才艺再高,也不可能写作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诗词。其次要学习他刻苦学习钻研、反复推敲提炼的作风。在整理父亲的遗物中,我们发现在他数十本工作笔记本的后面,都是写作诗词的手稿,上面全是密密麻麻反复修改的痕迹。有些诗句反复修改达五、六次,有些诗词反复推敲至完成长达一年多时间。在父亲去世前,只要还有精神,他都坚持阅读古典诗词。这一点,很值得年轻一辈的作者认真学习。
我衷心祝愿《杨应彬诗词》研讨会圆满成功,更希望在这次研讨会后,能够让我们岭南诗坛这个文艺百花园里,开出更多更艳丽的奇花异卉!我想,这也是父亲的最大遗愿。
最后我还有一个提议:我个人认为,30多年来杨应彬同志作为岭南诗坛的领军人物,不仅满腔热情地支持和推动广东诗词界的发展,而且以锲而不舍的辛勤耕耘,创作了1000多首脍炙人口的当代诗词,他赋予中国古典诗词全新的时代精神和思想内涵,将格律诗词和其他古典诗词强大的生命力,十分准确地、生动地、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性地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充分展现,成为我省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杨应彬诗词》在国内以及海外华人社会中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一个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影响作用。为此,我提议,请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和省中华诗词学会研究,是否能够把《杨应彬诗词》作为广东文学界的一个优秀作品向中国作协申报鲁迅文学奖。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