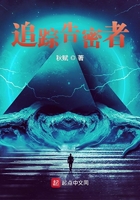
第89章 魔都病人(2)
我没想到,刘良昆跟着我也下了火车,好在只开出了一站,我们在苏州站没有出站,又上了回上海的火车,刘良昆带我走到5号车厢的字号边等着火车,上车后我才知道,这是餐车,买了两份中饭,我俩把饭吃完,正好又回到上海。
赶回到吴寂寞的家,只有保洁阿姨在,説她去昆山了,明天才能回。
我留下了字条,注明明天早上来拜访,有新的情况发现,当面谈。
现在我们俩背着包到哪里去?
他翻开手机,对我説:
“老师转过来一个病人,原以为没时间,不接了,现在看来正好还有一下午和一夜的时间,不如配合我去看看病人?”
在他的眼里,哪儿都是病人。
很快,他的老师约好病人,下午到晚上的时间,都方便去拜访。
“不会有危险吧?”我一直在想,他来上海,没有第一时间去看这个病人,一定是非常难看的病。
“情况不太清楚,老师説是妄想症患者,他夫人叙述的病情史,非常有故事性,今天他夫人不在,请的阿姨在家,阿姨都不怕,想必只是文疯子。”
我脑中出现了张之的情形,他对别人没有伤害性,只是伤害自己和家人。
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吃了点东西,刘良昆叫上了一辆出租车去浦东病人家。
上海的出租车非常干净,我刚夸完,司机回答:
“每天再晚收车也要自己清洗一遍,坐垫套都是一客一换的,累点,但是客人高兴,我们是服务行业对不对?”
一路上,他象主人一样,介绍上海滩的新鲜事:
“南京路上新开了一家百货公司看没看过?”
我摇摇头,逛店那是女士的专宠。
“歌剧院去看过伐?老高级的。”
我又摇摇头,BJ的国家大剧院都没去看过几场。
“来做生意的吧?”
看来他是非要拷问出我们的来沪目的,颇有朝阳群众的觉悟。
看来两个大男人挤在一辆车后座上,还沉默不语,背着极其普通的双肩背,而不是手提包,在车上也不打电话,长时间的沉默,这让他产生了怀疑。
“我是病人,他是医生,不是传染病,是精神病。”
我微微一笑解释。
司机紧张起来,一句话也不説了。
这位病人住的地方非常偏,左拐右拐,很顺利地到达小区。我夸着师傅不开导航也能找到,他説上海每个月要抽查考一次司机,考官伪装成客人,找不到路的或绕路的,都要进学习班,所以记住路那是基本功。
“我看你蛮正常的嘛。”
“治好的,医生医术高明。”
“这是你家吗,这是沪上一级鼎的高档小区。”
他眼中充同满了羡慕。
“很早前买的,当时相当便宜。”我拉近和他的距离。
他给我留了电话,説如果需要服务的话,给他打电话就行。
高档小区住户的门铃设在院门口,与阿姨通完话后,她打开了门锁。
穿过长长的花园通道,终于找到了独栋的别墅,一个穿着大红色棉睡衣的男人,站在门口迎接。
“陈刚,哪位是刘医生?”
“我是,这位是我的助手小宋。”
“两位医生好。”他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客厅。
与吴寂寞家的老派花园洋房不同,新建的别墅不仅客厅宽大,而且挑空也高,足足两层的面积,牺牲给了大客厅。
墙上全挂着魔都的标志性照片,特别是一幅长达4米的全画幅图片,全景式地展现了浦东的全景,非常少见的作品。
我看了看作品名,写的是陈刚。
“就是我拍的。”他解释。
我认真地看着他,难道妄想症的人,都能拍出这样的照片?
他看我不相信,领着我去边上的一个房间,推开门,吓了我一跳:
整整一屋子的各种专业的灯,杂乱地堆在各处,仿佛走进去连脚都放不下。
“都是好几百万的家伙什。”他介绍。
接着他又推开了另一间房门。
这里有整齐的架子,一格一格白色的,全部放着他的照相机和镜头。
墙上有一张英文的证书。
刘良昆仔细地看后,惊讶地问:
“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会员?您?”
“是的,中国就两位,我是其中之一。”
这哪叫什么妄想,这完全是专业的高度。
我们回到客厅,阿姨拖着一个大塑料盆,里面足足有数百只乌龟,她问怎么处理?
“倒掉,全部倒到黄浦江里去。”他回答。
难道是放生?
“刚刚送走了五条狗,精力有限,没时间弄了。”
看他的口气与实物,并不像是在妄想自己是个有钱人,刚才我撇了一眼那些镜头,每个都是我舍不得买的,至少都在十万元以上。
他从保鲜柜里拿出两瓶依云的水,递给我和老刘。
刘良昆打开包,拿出了笔和纸,开始了他的职业询问:
“听老师说,你去咨询过几次,老师也不太好判断,你是否患了病,他刚刚被一位病人推倒骨折了,所以让我来做家访。”
“哦,严不严重?”他关切地问,显然是更希望老刘的老师能上门。
“至少要三个月才能下地,怕耽误您的事,所以派我上门。
根据您夫人的描述,説你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已经超过的比尔。盖茨,是这样吗?”
他陷入了沉思,缓缓地説:
“是这样的,我已经在国外待了近二十多年,这次回国发现,我买的股票已经大部分清空了,只剩下了30万元。”
“原来有多少?1000万元。这么多年来,应该是按照他们给我发来的信息看,早就利滚利了,我可是买的一手的银行股。”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炒股的失败者,把原来的钱全部委托操盘手操作,全部亏空了,然后又妄想自己赢利了。一千万在BJ连一套好地段的二室一厅都买不到,别説投入到股市里,那是大海中的一根针。
刘良昆仍然耐心地问: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股票?”
“我是中国最早一批买股票的人,新闻上有报道,那可是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闻,我们都上了新闻的。”
我依稀回忆起那时我还在读书。
“我一直委托操盘手不断地买进,那时的一千万,想当于现在的一个亿吧,那时才几支股?”
“您描述的与夫人和老师电话里说的不太一样,夫人説你是在做梦,那些股票都买亏了,现在家里就剩下这30万元,连狗都快养不起了,你还要去世界各地拍照片,所以她认为你不承认现实。”
刘良昆指出了残酷的现实。
他想了又想:
“不对啊,就是把钱那时候存到银行,也不会只剩下这30万元。”
道理是对的,但是股市有风险,人家在入门处都写了备注。
老刘收起笔记本,他已经知道了基本病情,好在病情还不严重。
他开了药,交给阿姨,让明天夫人回来后,去医院找老师留下的值班学生,重新开一份去药房领药。我撇了一眼龙飞凤舞的药方,感觉到医生写的字,只有他自己认得,怎么别的医生也认得呢?好象他们之间,通行着这种病人永远也看不懂的文字。
阿姨小心地收好了药方,把我们送出了院门。
陈刚一直跟着我们,我看见老刘趁着阿姨不注意时,在他的手心中,塞了张纸条。
“我留了你的电话,到时候你接下,再转我,你要判断,他在打电话时,身边有没有人监听。”
我明显地发现了他的紧张。
“为什么不留你的电话?”
他解释:
“是这样的,我发现陈刚没有病,他是正常人。”
“那你为什么还给他开药?”
“那只是些维他命,补充电解质的药,没什么大碍。”
“为何不当场説明呢?”
“阿姨在,我不能判断,她站在哪一方。”
“你的意思是,陈刚的病,是被人陷害的?”
他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