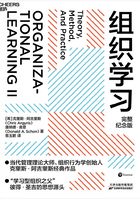
组织能够学习吗
20世纪70年代初,当我们初次提出组织学习的概念时,许多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认为这个词似乎有点儿神秘,甚至与黑格尔学派把集体拟人化(7)的做法有一些相似。显然,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个体才能思考、推理、持有某种观点,也只有个体才能学习。在他们看来,说组织在学习,即使不是违背常理的,也是自相矛盾的。
然而,在日常交流和学术沟通中,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思考、推理、记忆、学习等也可以是团队、部门或整个组织的活动。例如,人们常说“营销部门认识到销售额将会下降”或“行政部门学会了在宣布重组之前咨询全体顾问的意见”。在日常交流中,此类说法或许可被视为对某些隐含的复杂过程的简化。然而,在把组织视为认知者或学习者时,学者似乎刻意避免将个体现象与组织现象联系起来。
在把思考、认知、学习当作组织层面的事情时,如何才能显得自然而然且避免产生问题呢?人们似乎可以采取下列两个策略:
1.站在旁观者立场,把组织部门或子部门视为统一的整体;
2.把这个整体视为一个非个体的行动者。
要把组织视为非个体的行动者,就需要采用一种计算机语言,比如有人说“某种组织惯例长期存在并凌驾于其他惯例之上”,或者说“一般管理部门选择了研发部门提出的某个建议”。使用这类语言的人越来越多,这表明计算机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提高。随着计算机在组织中的普及,人们开始倾向于使用计算机语言来描述以往归类于思想、意志、深思、感觉或习惯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组织成员往往会不假思索地说“我正处于销售模式”“我没有被纳入这个任务程序”“这是我们的默认选项”。既然计算机能够实施某种行为、思考、记忆或认知,并且计算机系统能被视为聪明的或愚蠢的,那么组织或其各部门为什么不能呢?这个计算机隐喻的力量,也许会让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组织及其各部分视为非个体的行动者。
如果要把组织视为整体的非个体的行动者,站在旁观者立场对组织进行远距离观察就是一种恰当的做法,或许也是必需的。例如,研究企业理论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企业战略的理论学者往往会从外部观察商业组织,这样做可以看到一个整体,但整个组织也成了一个黑匣子。他们提到的企业往往指的是,为了在特定市场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而与其他企业竞争,并采取或改变某种战略的行动者。所有这类由远距离观察而来的组织行为理论都着眼于社会集体层面,可能会为经济理论甚至政策分析做出贡献,但并不会或并不试图描述和解释组织内部引发认知、思考、记忆、学习等行为的模式,也不涉及如何实现“有效的学习”(这个词还有待定义)。
因此,组织学习的理论学者若想要有效地指导实践者,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把组织学习与实践者的思考和行动联系起来。此外,即使理论学者没有考虑过要为实践者提供帮助,而只是试图为整体组织现象提供一种完整自洽且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他们也应该探索这种联系。
如果转换成外部旁观者的视角,即不把组织及其各部分视为非个体的行动者,而是从内部观察引发组织行为的个体过程和人际过程,我们就会再次陷入组织学习的悖论。或许,“组织学习”这个术语与“组织力”或“组织熵”一样都是比喻。我们说组织能够认知、记忆、思考、学习,这种说法有意义吗?我们又如何验证这一点呢?我们要想切实理解组织学习,就需要详细说明这些过程及其条件。
然而,无论可能存在多少困难,由于组织学习的悖论突破了人们的常规认知边界,因此可能会推动组织理论发展。为了深入探索组织学习,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所指的“组织”究竟是什么,也必须思考什么是学习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