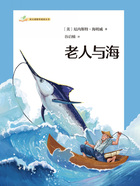
导读
谷启楠
《老人与海》的作者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是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老人与海》是他自认为“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1)。
一、海明威其人
根据《诺顿美国文学选集》和《牛津美国文学词典》等资料的介绍,1899年7月21日,海明威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橡树园镇。他的父亲是一位有成就的医生,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海明威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高中毕业后即到《堪萨斯城市之星》报社担任见习记者。1918年他在法国加入了红十字会急救队,去意大利前线运送物资,两个多星期后负伤,但抢救了一位伤得更重的战友。后来他受到意大利政府嘉奖,被尊崇为英雄。
1920年,海明威被《多伦多星报》派驻法国巴黎,结识了在那里侨居的美国知名作家葛特鲁德·斯泰恩、舍伍德·安德森、埃兹拉·庞德、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等,他们对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的影响。海明威从1923年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1925年,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出版。1926年,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使他开始享有国际声誉。
作为作家和战地记者,海明威一生中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1941年曾到访中国),参与过狩猎、斗牛、捕鱼等挑战男子汉勇气的活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西班牙内战,阅历极其丰富,思想极其深邃。他秉持反纳粹主义的立场,支持并参与多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在战火中写出许多新闻报道。他的文学创作一方面遵循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也发展了现代主义手法。在《没有女人的男人们》(1927)、《永别了,武器》(1929)、《富有的和没有的》(1937)、《丧钟为谁而鸣》(1940)等主要作品中,他塑造了众多在文明社会的残酷现实中英勇、坚毅、隐忍的“硬汉”形象,也塑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厌恶战争、丧失信仰、对社会绝望的人物形象,因而被称为西方“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言人。
1950年,在新作《过河入林》遭质疑后,海明威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退隐到古巴,开始创作小说《老人与海》。这部小说塑造了又一个不畏艰险、勇敢拼搏的“硬汉”形象,于1952年出版,并于1953年获得美国普利策小说奖。1954年10月,海明威以其文学成就,特别是《老人与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一生中有四段婚姻,三位妻子都是记者或作家。由于海明威1953年在非洲游猎途中曾连续两次遭遇飞机失事,他的身体和心理都受到极大的创伤。后来他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1961年7月2日,他在美国爱达荷州凯彻姆城家中用猎枪自杀。
海明威虽然离去,但身后仍有遗著出版,如回忆录《流动的盛宴》(1964)、小说《海流中的岛屿》(1970)等。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仍在影响着世人。
二、《老人与海》的解读密码
海明威与古巴有较深的渊源,早在1925年和1932年就访问过古巴。他同情古巴人民的革命斗争,与其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有过交往。1940年,海明威在离哈瓦那九英里的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镇买下“瞭望农庄”,1941年入住,《老人与海》就是在那里创作的。他常去科希马尔渔村,在那里拥有一艘“支柱号”渔船,常跟渔民一起下海捕鱼,十分熟悉他们的生活。
《老人与海》讲述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出海捕鱼的故事。由于他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他的助手、小伙子马诺林被父母安排跟了别的渔船。在第八十五天,圣地亚哥独自驾驶小帆船去远海捕鱼。经过两天半的努力,他终于捕到一条巨大的枪鱼。在带鱼返航途中,他的小船和绑在船体上的枪鱼多次遭到鲨鱼群的袭击,他随时都有丧命海中的危险。圣地亚哥历尽艰辛,顽强搏斗,虽然伤痕累累、筋疲力竭,还是把残存的巨大枪鱼骨架带回了渔港。
这部小说内涵丰富,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层面解读。简而言之,它既是一部描写个人捕鱼经历的小说,又是一则宣示人类命运的寓言。
作为描写个人捕鱼经历的小说,《老人与海》有真实的背景:故事发生在1950年9月,地点是古巴科希马尔渔村及其濒临的海域。虽然海明威生前声称,圣地亚哥是个虚构的人物,没有任何原型,但当地的渔民仍认为,海明威的朋友、渔夫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是主要的原型。1999年,美国《纽瓦克明星记事报》的记者布莱恩·弗朗西斯·多诺修访问了科希马尔村,有幸见到已101岁高龄的富恩特斯。老渔夫肯定地说,《老人与海》是“虚构小说”,但认为这个故事发端于海明威初来渔村时所听到的关于一个20岁的小伙子(即富恩特斯本人)在小船上独斗巨大鱼的故事。记者也采访了86岁的渔夫何塞·赫曼德兹,他曾在1945年与两个同伴一起驾小船捕到过一条长21英尺、重约7000磅的大鲨鱼,并拍下手持鲨鱼骨架的照片为证。记者还采访了74岁的渔夫奥斯瓦尔多·卡梅罗,他虽已退休,但每天坚持下海捕鱼。此外,记者也听到了其他几个渔夫的故事。(2)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圣地亚哥虽然是个虚构的人物,但集合了诸多渔民的特点,是他们的最完美的代表。
一方面,海明威用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了大海的壮阔、海鸟的灵敏、枪鱼的狡黠、鲨鱼的凶猛,生动地描绘了圣地亚哥捕鱼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他又用现代主义手法展现老渔夫的内心独白,揭示出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圣地亚哥善良、谦和、勇敢、顽强、坚忍,崇拜坚毅的棒球明星迪马乔,专注于传统的捕鱼技艺,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他说:“人生来不可被打败。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此语表明了他的价值观,已成了警世名言。马诺林受到他的影响,认同他的价值观,愿意继续跟他一起捕鱼,迫切希望向他学习更多的传统技艺,与那些一心追逐商业利益的年轻渔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海明威曾说:“这个奖属于古巴,因为我这本书是在古巴构思和创作的,与我的科希马尔村的村民一起,我是那里的公民。”因此他把他的诺贝尔奖章供奉给了古巴保护神“科夫雷的圣母”。(3)
除了现实主义的意义,《老人与海》也是一则宣示人类命运的寓言。它探讨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书中的太阳、星星、风儿、大海、海鱼、海鸟、海藻等都是大自然的构成因素。圣地亚哥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物杀一物。捕鱼要我的命,正如捕鱼让我活命。”他终生与大海为伴,靠着大海的慷慨馈赠来生存;而大海则变幻莫测,既非仁慈,又非邪恶,既能帮助人,又能毁灭人。他以捕鱼为生,把某些鱼类视为自己的兄弟,但为了维持生计又必须捕杀它们。而鱼类在养活人的同时,为了生存也常置人于死地。这就是人与自然相生相克、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类必须正确认识这种关系,学会与大自然和谐共存。
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圣地亚哥竭尽全力,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取得了微弱的胜利,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圣地亚哥不仅是一位真实可信的渔夫,更可被视为人类的代表。通过他的故事,海明威讴歌了人类坚韧不拔的“硬汉”精神。所谓“硬汉”,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在很多情况下,“硬汉”是普通人,但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在逆境中不畏艰险,忍辱负重,虽然失败仍保持尊严,面对死亡仍表现出“压力下的优雅风度”(4)。正如海明威所言:“这本书描写一个人的能耐可以达到什么程度,描写人的灵魂的尊严,而又没有把‘灵魂’二字用大写字母标出来。”(5)
三、海明威的写作风格
根据美国作家卡洛斯·贝克写的传记《海明威:作为艺术家的作家》,海明威是记者出身,早年他在《多伦多星报》任职时,该报文学部要求记者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写作:“叙述有意思的事情”“用短句”“写陈述句”“用生动的语言”“避免用陈腐的形容词”“力求通顺”等等。通过写新闻报道的历练,海明威形成了平实而简朴的写作风格。
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以精练的语言和简明的句式来叙述故事,重点在于展示,而不是讲解。他十分重视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圣地亚哥独自在海上捕鱼,没有人可以交谈,但他的思想很活跃,渴望表达。他一方面要随时应对现实的危机,另一方面又会联想起过往的经历。因此描写他的内心独白和心理联想,成了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
根据《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第5版)的介绍,海明威曾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我一直力图根据冰山原则来写作。每座冰山除了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隐在水下。”海明威独特的文风影响了后世的许多作家。瑞典文学院授予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时,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他精通叙事艺术,这表现在他最近的作品《老人与海》中,也因为他对当代文学风格产生的影响。”(6)寥寥数语,道出了海明威作品的魅力。
海明威告诉我们:“真正优秀的作品,不管你读多少遍,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写成的。这是因为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有神秘之处,而这种神秘之处是分离不出来的。它继续存在着,永远有生命力。你每重读一遍,你看得到或学得到新的东西。”(7)这就是说,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有丰富的内涵,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理解和想象的空间。
建议读者根据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来阅读《老人与海》,以发现更多的精彩,获得更多的启示。
(1) 参见海明威《致华莱士·梅耶,瞭望农场,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与七日》,董衡巽编选《海明威谈创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40页。
(2) 参见Donohue,Brian Frances. Hemingway’s Cuba:The Old Man and the Sea,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2.
(3) 参见Vanona,Anoldo,ed. Ernest Hemingway in Cuba:Old Man and the Sea.引文自译。
(4) 海明威在1926年4月11日致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信中首次提出“压力下的优雅风度”这个说法。1929年11月30日出版的《纽约人》杂志刊登了专访海明威的文章《艺术家的报偿》。文中说,多萝西·帕克问海明威:“你所说的勇气到底指什么?”海明威回答:“我指的是,‘压力下的优雅风度’。”
(5) 参见海明威《致华莱士·梅耶,瞭望农场,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与七日》,董衡巽编选《海明威谈创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43页。
(6) 参见“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54”. Nobelprize.org.July 24,2012.引文自译。
(7) 参见海明威《致哈维布雷特,瞭望农场,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董衡巽编选《海明威谈创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52页。